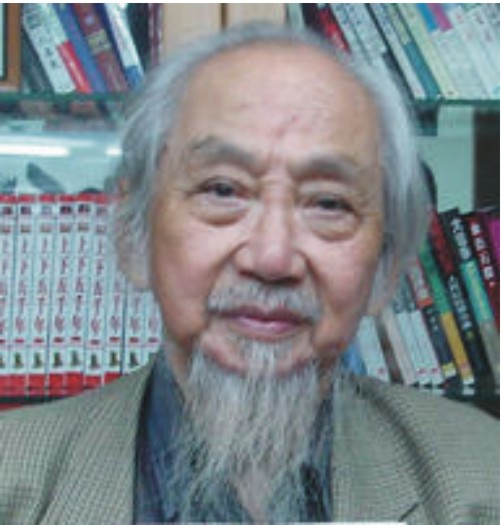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 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比、兴”——论中国绘画的抽象审美意识 |
| http://www.zhuokearts.com 2010-09-15 新闻来源:《重要的不是艺术》 |
|
相关链接:论实验水墨与抽象 西方画家多遵循亚里士多德“艺术本于摹仿”的理论,趋向于人物、风景物象的形式再现。而中国古典画家则不同,他们对山水花鸟,以至一木一石的刻画,不追求模仿写实。所谓“为山河传神”,其真正含义诚如恽南田所说:“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画论丛刊•南田画跋》)实际上,就作为自然对象的山水花鸟本身而言,本无所谓“神”的。人们赞美、刻画松的坚贞,兰竹的秀逸,与其说是因为这些自然景物具有某种所谓“坚贞、秀逸”的精神,毋宁说是人的精神在这些自然物中对象化了——这些气质神韵其实只属于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而并非属于作为审美对象的物。是人在梅的傲雪、松的苍翠、竹的劲挺之中,找到了自己这种气节情操的寄托和象征物。这也就是古人所谓“托物见志”、“缘物寄情”的含义。 这种主体精神情操的深刻内涵,以及中国古典艺术家对于山水、松竹、花鸟等审美象征物的发现和有意识表现,构成了唐宋以后——特别是异军突起的“文人画”的艺术主题和基本特质,从而深刻地在作品中创造了迥异于西洋绘画的艺术意境和美学表现。 (一) 悲秋风于落叶,感春华而兴情 悲秋风于落叶,感春华而兴情,心情畅快见溪流犹闻欢唱,时逢伤心听溪流又仿佛变成呜咽。此类心理经验人皆有之,其实这正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一种创造活动,是人通过自然物象寄托主体情思的审美活动。生活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处在某种精神状态中时,常常由于周围景物的某种特征和自己精神状态的凑然合拍,而引起共鸣,或者从自然景物中看到和自己精神相吻合的特征而加剧某种感情的冲动和释放。另一种是触景而后生情,即在某些自然景物面前唤起了心中某种和自然合拍的情感。如危耸的峭壁唤起人的崇高感,而淙淙碧溪则引动人的优雅感等等。这种心理“创作活动”的本质,都在于主体从自然对象中获得了某种精神对象的发现,即通过创造性的“物我交感”而表达出人的某种审美情感来。从这个角度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一般人创造的寄托他审美情感的自然物象,仅仅停留在感觉中;而艺术家却把这种感觉通过语言再度物化了。前者仅是审美活动,后者则升华为艺术创造。 艺术的审美活动,总是通过审美感受和审美情感两个层次来实现的。审美感受,是最初触动人内在情感的那个自然物象在人心中留下的第一印象,但这绝不是对于自然物象的模拟。心理学对人视觉的研究表明,人对事物的注意所获得的印象,受观察者心理状态的制约,往往是通过主体心理结构的加工而变了形的意象。因此,从对象获得的审美感受,被捕捉的往往是与主体自身的审美情感最相契合的那些特征。尤其当这种感受和情感交融之后,留在人印象中的这种特征会愈加鲜明。中国古代在创作方法上的所谓“遗忘法”,其实就是抓住这愈加鲜明的符合审美主体某种精神的物象特征,从而使艺术作品母题明朗化的。这也就是艺术家笔下的自然物象之所以比客观的本来物象的特征更加鲜明的原因。“米点山水”所表现的江南水乡那种烟雾朦胧的感受,实际上比实景更集中更动人。正如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即是对“晨晴晦雨间”那种“不可名状神奇之趣”的表达一样,审美感受往往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一瞬间触动人的心灵,它是直觉的而非理智的逻辑化了的,所以常常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 而审美情感,则是来自社会生活实践所引起的各种思想感情,层层沉积在人的心中,一旦遇到相应的表现形式,这种情感便会骤然得到喷发,从而结晶为一件作品。这种升华为艺术作品的情感必然是审美的。因为在作品中,这种情感“净化”——或者说形式化了。《红楼梦》中黛玉的悲愁通过落花而抒发,落花所体现的悲愁就是黛玉的审美情感,在没有得到抒发以前则只是痛苦而已。亚里士多德论悲剧认为,艺术具有对情感的洗涤净化作用,其根本道理亦即在此。 在审美感受和审美情感中,后者不但是更深层的,而且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人只注意和情感相吻合的自然物象的特征,不同的人在同样的自然物象面前会产生不同的美感;所谓自然美,都不过是这种主体审美情感外化的结果,无论是一般人感觉中的美,还是艺术创造的美,莫不如此。 (二)山水花鸟画的实践中的)“托物见志” 在中国古典绘画史上,“托物见志”的艺术表现广泛见于山水花鸟画的实践,虽在宋元之际,但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却可远溯于先秦。诸子著作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如孔子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篇》)。刘宝楠《论语正义》注说:“言仁者愿比德于山,故乐山也。”《说苑•杂言篇》又说:“子贡问日:‘君子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日:‘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旬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人,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率吾其性。”等等。这种以自然和“君子比德”才显示美的观点,并非诸子个人的审美趣味,它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国人相当普遍的一种自然审美观念,这还可以从《诗经》、《楚辞》的大量作品中得到证实。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渗透和凝练着超自然而属于人的感情色彩。到刘勰“比、兴”说的创立,则使这种创作方式在理论上更趋系统和成熟。此后无论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还是理论,对“比、兴”的阐述和动用,都有所进展,以至出现了盛唐诗歌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大时代。 诗和画常被称作姊妹艺术。故古人向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的说法。这不仅说画中常以诗作配,更主要的是在审美原理上,这两大艺术常有相通之旨趣。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讲究“空灵”、“意境”、“言在意外”,司空图《诗品》中所提出的美学范畴如:雄浑、冲淡、纤称、沉着、高古等等,无一不可见之于中国古典绘画美学原理中。 所以,其一,我们以为中国这种审美观念的源远流长和经久不衰,决非偶然,而是民族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结构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二,中国的古典美学在原则上根本不同于西方古典美学。实际上在西方美学观点中,“移情说”的理论直到18~19世纪才出现。在此之前居理论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艺术的“摹仿说”。而中国却从来没有把摹拟作为艺术的目的,而总是着眼于更自由地表现作为人的主体精神。这种美学观念,为唐宋以后大批以审美表现为内容的山水花鸟画,和宋元以后异军突起于画坛的“文人画”,奠定了深刻的美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绘画理论中的抽象审美意识 中国绘画理论,在其早期著作中,以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及萧绎《山水松石格》为最有价值和见地。宗炳论绘艺之宗旨认为,绘画是“圣人含道哄物”、“以神法道”,是“山水以形媚道”。王微则认为绘画的目的“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是“拟太虚之体”的虚,本于老子“渺渺冥冥,其中有物”的大道。而萧绎则主张,画艺应“运人情”而“设奇巧之体势,写山之纵横”。总之,在所有这些尚属于中国古典绘画美学奠基期的著作中,我们已可以看出此后贯穿中国古典造型艺术近二千年的基本原则——即以人的精神意识为主体,以画的题材为形式,主张对题材作人性化、性灵化的处理。就山水花鸟画而言,要使山川木石皆成为表现主体性灵的形式,形式不必尽求真确(即形似),但表现的性灵必须有深奥的意境寄托(即神似)——这种抽象的主体表现化的审美意识,乃是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形神观念的真谛之所在。其影响无比深远。不理解这种抽象审美意识,对于其后的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就根本不可能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 当然,就作品看,宗炳时期的山水画已不复见到,隋唐的山水画又尚处于幼年时期,即使是盛唐时李思训这样的大家,也还在追求对自然本身感受的如实描绘。但是,由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早成,毛笔的长于“写”而不长于摹拟,以及石青石绿的色彩上那种超自然的特征,就限制了写真画艺的发展,然而却酿成了这位唐宗室画家作品中的那种富贵气,这恰恰不是自然所给予他的启示,而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带给他的审美情感的结果,从而使这种艺术表现也在审美的主体化中超越了对自然物象的相对忠实。而在号称谓“南宗”画祖王维的作品中,淡墨的渲染,一洗传统的勾勒填色,实际上已在开拓中国古典绘画走向流变的崭新方向。而后经张躁、荆、关、董、巨、郭、米氏父子,到元四大家便形成了与李派浓妆艳抹风格迥不相同的水墨画风。虽然董其昌袭用禅学分南北宗的套式,区分李思训与王维开创的不同画风,早即受到美术史论家的批评,但董认为文人画“自王维始”,苏东坡亦称“吾于维也无问然”,则却是有道理的。至于董氏认为“北宗”“为造物所役”;南宗“寄乐于画”,则又和苏氏论王维、吴道子画所说的“吴生虽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同出一辙。这里不仅强调王维及“文人画”的画格高于吴道子和所谓“北宗”画家,而且指出其高妙之处在于对形象的超越——即抽象性灵的表现,确是抓住了中国绘画美学的精髓。 宋代是中国古典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繁荣时期,就流派之繁多,画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超过此前和此后的任何时代。就对于表现主体性灵的自觉程度而论,我们又可以看到如下三种类型。一是院体画(尽管并非全部),崇尚“刻意求工”。如众所周知的徽宗赞赏能画出四时朝暮花蕊叶不同的画家,以“孔雀升高必先举右”这种自然特性评定艺术作品的优劣。二是追求“意境”。在理论上,郭熙为集大成者,他在《林泉高致》中把“可游可居”作为“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的最高境界。三是苏轼提出“士人画”的概念,自觉地标出新帜对峙于院体画。主张“不求形似”得之于象外,“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他曾称赞文同的墨竹说:“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按指竹)独不顾。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墨君堂记》)这种把竹人格化的论述,正表明他们主张山水花鸟画是“逸人高士”对于自我人格的表现。 如前所说,由于中国笔墨工具和书法美学的制约,院体画的摹拟写实风格始终未涌作巨流。而院体画中的佳作,却常是不自觉地表现了作家的自我性灵而跃登上品。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于细丽典雅的色彩装饰中透出的富丽堂皇之感,打破空间的局限,把千里江山浓缩于卷幅之间的广阔之感,并非摹拟之功。就连传为宋徽宗本人的《芙蓉锦鸡》之所以被称为名作,也是由于他成功地表现了雍容华贵的审美情感,然这雍容华贵却非芙蓉、锦鸡的自然属性,而是作者性灵的外化。 所谓意境,其实就是审美主体中和自然物象特征相吻合的心境,即个人描绘中一个表现出的对自然物象某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这类作品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诸诗属同一类型。王国维称之为“无我之境”,其实这正是对特定环境在人的心中被高度纯化、净化后的感受的表达。如范宽的山雄浑丰厚,马远、夏圭的山峻峭挺拔,米友仁的山空潆秀润,这种意境的不同,都在不同程度上映照着画家个人性灵以及彼时彼地心情的不同。 至于“士人画”中,可举东坡的《古木怪石图》,如他在另一幅同样作品的题诗中所说:“枯肠得酒芒角生,肺肝槎橱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7)显然,画中的古木怪石,犹如《石头记》中的怪石一样,纯然是作家精神的象征,因此邓椿在《画继》中评说:“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这里已更深刻地触及到了此类艺术品种的本质——能够更自由地创造一个寄托主体审美情感的“自然物象”,此“自然物象”更少地受自然真实物象的制约,甚至可以完全不吻合。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都包含着一个表现主体性灵这个内核,不过在院体佳作那里不是自觉;在第二类那里是外化于自然某种特征;在实质属于抽象表现的“文人画”中,画家的情感和性灵便得到了更全面的表现,所以往往触及人心灵中的更深层,作品亦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即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空灵”之境。 这种追求主体境界的抽象审美意识,到元四大家蔚为大成,明清达到了高峰。出现了徐渭、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这样的大师。其作品如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那种奇特的丘壑、疏落的枯树、如墨的天气,所传达的冷峻和阴郁,实是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沉郁心情的表达。这种情感在倪瓒的作品中尤为突出,萧涤淡?自的丘陵,冷落稀疏的小树,几乎充斥了他所有的作品,这显然和他处在明媚秀丽的江南水乡的自然特征极不吻合。同一个江南水乡,在赵孟兆页的笔下是那样的秀润清爽,和倪瓒相比,又是何等不同的审美情感!再看徐渭的墨葡萄,那决非对累累果实的欣赏,乃是愁肠郁结的寄托。所以他题诗于其上:“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朱耷瞪眼的鸟,丑陋的孔雀,已无法找到鸟的活泼可爱,孔雀的色彩斑斓这些自然特征的影子,但却成为这位明遗老愤世之情的真实写照。至于石涛那些荒山古径,老树落叶;以及郑板桥的风竹等等,无不深沉地浸润着生活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这些落魄书生以及避世遁入空门者的积郁、孤傲和冷峻。所谓“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郑板桥诗)。以及“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理,几人抛却故纸横着自家鼻儿也?”(张怡题渐江画册句)这些傲世之词,也正是他们的艺术创作作为自身情感外化物的写照。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美学观的形成,其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尽管时而出现摹拟自然的现象,模仿古人之风亦曾一度盛行,但它却一直顽强地左右着汉民族古典的审美意识。所以说文人画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发展的必然产物。 (四)中国古典山水花鸟浓缩和净化的抽象性 中国古典山水花鸟画追求的那种主体性灵的美,即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诸如雄浑、冲淡、高古等范畴。它是人的社会地位、经历、思想、个性等,被高度浓缩和净化的带有抽象性的一般情态的美。 其一,它可以超越社会学范畴的各种具体特性,呈现出一种带有共同人性的特征。就如同忧愁的产生有着千差万别的原因,但忧愁的情感状态却具有同构性。民族传统意识把看到喜鹊当作吉利的预兆,从审美属性说,是一种通感,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喜悦内容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但却共同创造了一个“艺术品”——象征喜事的喜鹊。宋徽宗的《芙蓉锦鸡》被历代奉为名作,也正因它成功地表现了一般的富丽华贵的精神情态。因是一般情态,就不只存在于皇帝和富有阶级中,我们也可以从大量的民问艺术品(诸如窗花、对联、门帘等)中发现“荣华富贵”、“福禄寿喜”的字样及情调。所以,对于只表达一般情态的富丽华贵,而并未揭示或超越了它产生的阶级和社会根源的《芙蓉锦鸡》来说,二者具有相通的因素。这也是它能够在不同时代、阶级,但有相类似情感状态的人们心中引起共鸣的原因。 其二,有人说,旧山水花鸟画多是表现士大夫的享乐、消极的感情,而人民与自然的关系是积极的,新的山水画就应该体现出积极、健康的精神来。当然,这应该是一种美。但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某种相类似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而人民和自然的关系却永远是积极的,并且越来越能够掌握它。如果就此推论,我们实在无法想像以后的山水花鸟画所表达的会永远是直线上升的积极情感。这种观点,其实把本来是自然科学范畴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于艺术范畴里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自然物象在此类作品中不过是情感的象征,作品的优劣,也向来不是以作品对自然本身规律掌握和描绘的多寡来论定,而总是看是否表达出那个时代的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状态来。而且,中国自古多以此来品评作品,如谢赫称卫协“颇得壮气”,陆绥“风采飘然”,张则“意思横逸”,刘顼“用意绵密”等等。这一点和品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原则。所以,这种主体性灵的一般情态性和抽象性,就成为对于任何其他科学所无法替代和把握的内核——艺术的灵魂。 (五)通感——笔通情墨通趣 中国画论中关于“笔情墨趣”的论述,即强调笔墨挥洒处即人的审美情感的外化,是一个很精辟的美学思想。精辟在它表明了艺术作品中的笔墨本身有完整的审美价值,它不仅是描写那个客观对象的手段,而是可以直接表达人心灵中的审美情感的。这一审美命题发源于书法美学,又光大于绘画美学,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特色之一。 王羲之论书说:“夫纸者,阵也……心意者,将军也。”“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题笔阵图后》)以及中国绘画不称“画”而称“写”等,正表明中国书画具有相同的艺术目的和共性,这种艺术共性正是书画的抽象表现美。我们可以从《自叙帖》中感受到怀素的狂放;从《争座位碑》中感受到颜鲁公的愤怒,就是靠这些作品的“笔情墨趣”来体会的。而古人在评画时,也同样通过用笔来品评作品的美学价值。例如张彦远的画论曾有:“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陆探微精利润媚。”“张僧繇点曳斫拂……钩戟利剑森森然”等说法。加以中国书画使用相同的工具,很容易使书法的笔法入画。“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历代名画记》)其后陆探微以其笔法人画,创成“一笔画”。 笔情墨趣在具体作品中常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强调审美感受,笔墨挥洒既是和人的精神相吻合的自然物象某些特征,又是作者在自然物象特征中所寄托的情感;另一种,笔墨不但不吻合自然物象特征,而且与之相抵牾,更多地凝聚着主体的审美情感。如石鲁在“文革”中画的兰,那种极不畅快地堆垒着的干枯的墨团,仿佛每“推”半寸都很困难的用笔,显然和舒展的兰叶特征极不吻合,但却充分表现了作者当时痛苦、压抑的心情。 笔墨对于审美情感这个信息的传达,是靠用笔(特定情绪下用笔的轻、重、缓、急等)、用墨(墨迹所形成的干、湿、浓、淡、层次等)。前者像音乐家演奏乐曲时因情绪所产生的律动效果,后者则像不同乐章乐音的结构。亦正如音乐中这两者交谱合一成为情感符号一样,特定情绪、心理状态下的笔墨运用,亦会传达出画家特定的创作情绪。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靠人的审美“通感”而达到沟通。如前所谈及的石鲁的兰,它是靠墨团的“干枯”、“行笔的困难”与人的“心情不畅快”之问的某种同构关系,而使人产生通感的。 主体性灵的抽象性和用笔用墨的抽象性,正是二者的这种对应的同步关系,才能使人通过笔墨的挥洒,感受到那种任何别的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主体性灵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绘画有类于音乐。音乐在传达情感时的抽象性,以及它作为艺术表现的抽象性,几乎可以作为把握所有艺术的共同特征。 综上所论,一是追求艺术对主体精神境界的自觉表现(表现论),二是渗透在作品中的抽象审美意识(抽象美),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古典绘画的基本美学特征。 这两大特征,在美学原理和艺术表现上,即形成了中国传统绘画与现代派以前的西洋绘画极为不同的美学风格。所以,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洋画法传人中国后,西洋画的透视法、构图法和写实技巧,非但根本不为中国艺术家所接受,而且从根本原理上受到断然的拒绝和排斥。如清末张浦心曾说:“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人,通中国语,来南都,……画其教主(基督母)抱一小儿为天子(耶稣)像,神气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日: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画兼阴阳,教四面皆圆满也。……焦氏(伯贞)得其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 这种对于西洋绘技的轻视,正体现了在艺术表现和审美意识上,中国古典绘画追求抽象表现美,与西方(在现代艺术产生前)追求模仿写实美的深刻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