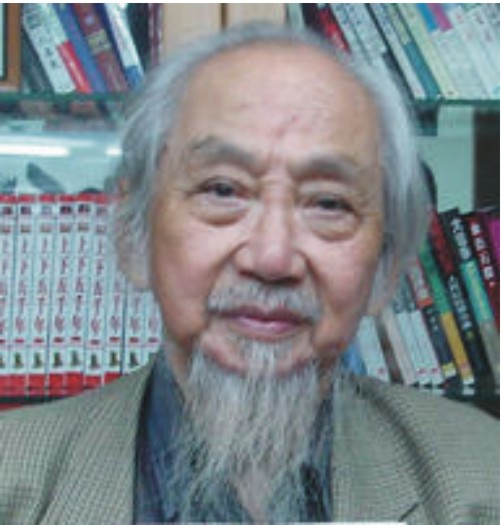演艺“非遗”活态却活力不足
论及“非遗”,我想把话题限定在“非遗”中的演艺品类方面。事实上,演艺作为“非遗”,是“非遗”的主体部分和主导方面。否则,2001年以全票通过而位于世界首批“非遗”名录之首的就不会是昆曲,而此后也不会有古琴、木卡姆、长调等的接踵而至。演艺“非遗”之所以会成为“非遗”的主体部分和主导方面,正在于它集中、典型地体现了“非遗”的活态特性——它不同于许多“非遗”名录中产品形态与生产者“物我两分”的项目,而是始终体现为生产者与产品形态的“不可剥离性”。这种生产者和产品形态的“不可剥离性”才真正是“非遗”的本质,这个本质是“非遗”作为“活遗产”的内在规定性,是彻底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意识及其直接呈现而非“物我两分”的遗产。其产品形态固然也物化为一定的物质形态,但这种物质形态始终由生产的意识和技能所驱动而变动不居。“活遗产”就体现在这种“变动不居”的物质形态或者说是物化状态中。
“非遗”之所以成为当前声势浩大的文化景观,一个可以直觉到的现象是它需要“保护”。因为,在经济社会迅速转型并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绝大部分由农耕文明滋生并养育的演艺品类都显得活力不足了。但“活力不足”并不等于“濒危”,而是否“濒危”其实才是“非遗”列入名录加以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演艺“非遗”中,600余年的昆曲雄赳赳名列榜首,而许多不足百年的小品类也乐滋滋叨陪末座。弄得像个水浒梁山的“聚义堂”,怡然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我看来,很多演艺“非遗”其实远未“濒危”,有些甚至还魅力四射活力十足。但不如为何这些演艺的从业者也忧心忡忡,唯恐不能列入“非遗”而生“遗珠之憾”。在许多情形中,他们的心态其实比演艺当下的状态更老态。
演艺“非遗”要在形态创新中实现活态生存
有人说演艺“非遗”的申报与确认有些像我国经济建设中“贫困地区”的申报和确认。经济的贫因,有地区不可变易(或者叫不可逆转)的生态因素在起主要作用,但申报并被确认成为贫困地区需要一定的“贫困指数”来考量。这在我们“非遗”名录申报中起码是不完备的。既然演艺“非遗”需要保护的最大问题是活力不足,那我们对列入“非遗”项目的演艺品类至少有一个“濒危指数”对之加以考量(事实上,“文化价值含量指数”也是必须的)。“非遗”名录的巨大和众多,并不只是显示出我们“精神家园”曾经的富有,肯定还意味着这个“精神家园”当下的危机。我们注意到,正如有不少“贫困地区”即便经济有所改善也迟迟不愿“摘帽”,原因在于对国家扶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在有些地区甚至体现为放弃生产自救而放任生命沉沦。“非遗”名录一批接一批地公布,是好事也要警惕其负面效应——那就是有不少“活力指数”尚可的演艺“非遗”在列入名录寻到保护后,其“活力指数”愈保护愈低下,最后还真的成了“濒危”甚至真的走向“危亡”。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非遗”名录的公布在于关注它的“濒危指数”并从而激发它的“生存活力”,在于我们的演艺“非遗”要在危机中寻“转机”焕“生机”。事实上,演艺“非遗”的活力激发要害在于能否与时俱进,增强“活力指数”而削减“濒危指数”是我们面对种种“活遗产”的第一要务。
关于“非遗”的活态特性,已引起了研究者足够的关注;但如何让这个“活态”真正鲜活并为“非遗”注入活力,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良方”甚至还不能说完全开对了“药方”。我之所以看重“非遗”的“活遗产”特性,就在于这种特性中具有“生长性”;我们的“非遗”保护就应该激发其生长的活力并促使其自由的生长。但其实,演艺“非遗”的名录昭示者和活态传承者未必作如是观。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要求像对“物质文化遗产”(文物)那样来对待“非遗”,要求原汁原味,要求亦步亦趋,要求胶柱鼓瑟,要求守株待兔……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为种种“濒危指数”不同的演艺“非遗”营造或再造已经发生改变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的文化生态。不用深说,人们就知道相对于盖一座座宏伟壮观的博物馆来保存“文物”,面对“非遗”的“文心”,我们事实上难以固守由活生生的人群构成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的变易是时代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你喜好与否,它才是绝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道理”。我们说演艺“非遗”要在形态创新中实现活态生存,既是历史的镜鉴也是现实的昭示:比如有600余年历史的昆曲本身就呈现为一个活态的生长过程,它有过辉煌、有过凋零,更有过“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再生。这个再生就是在形态创新中实现活态生存。又比如有400余年历史的芭蕾似乎从未考虑申请名录“非遗”。在它看来,发展流派、追逐时潮、驰骋各国舞台是比跻身“非遗”名录更为重要的事情。
昆曲带给演艺“非遗”的启示
50年前,昆曲一出《十五贯》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而50年后,我们却要为它全票当选为“非遗”之首而额首弹冠。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却总觉得不是滋味。或许,“一个剧种”的兴亡衰替,并不决定于“一出戏”的有无。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总没有与时俱进、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出戏”,“一个剧种”无论怎样抢救和保护都难以改变“濒危”的命运。最近时有复排全本某剧的事情发生,我以为对于“非遗”的活态生存而言,这其实是一种“负增长”;同时,我也认为目前不论“濒危指数”如何都跻身“非遗”名录的做法,是未必有助于演艺“非遗”活力激发的“泛遗产化”状态。回到“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尽管这是个带有某种情感夸饰的说法,但却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认识:首先,一个剧种是否具有活力,主要体现为是否有一出或若干出“戏”活跃在剧坛,活跃在观众口碑之中。其次,一个剧种是否具有活力,要看这个剧种是否具有生长性,其剧目(戏)不仅体现为传统文化范式的守望而且体现为时代生活体验的延伸。第三,一个剧种是否具有活力,还要看这个剧种的生存是否具有包容性,在“敝帚自珍”的同时亦不排斥“他山之石”。要言之,一出戏之所以能救活一个剧种,在于这出戏能创新剧种的范式,更新剧种的内涵,刷新剧种的轨迹……我国“非遗”抢救、保护、扶持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我希望我们的演艺“非遗”多想想“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既便是“非遗”,也要追求有质量的生存,有价值的生存,而这必然也就是有生机的、能生长的生存。我们要关注“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复兴而不是总去做“一个剧种救活一出或几出戏”的复古。老演老戏,老戏老演将使我们彻底丧失“文心”而成为“文物”,那时“非遗”也就不是“非遗”了。上海昆剧院《班昭》、浙江昆剧院《公孙子都》等的问世,体现出古老昆曲在形态创新中实现活态生存的追求。这值得我们演艺“非遗”关注并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