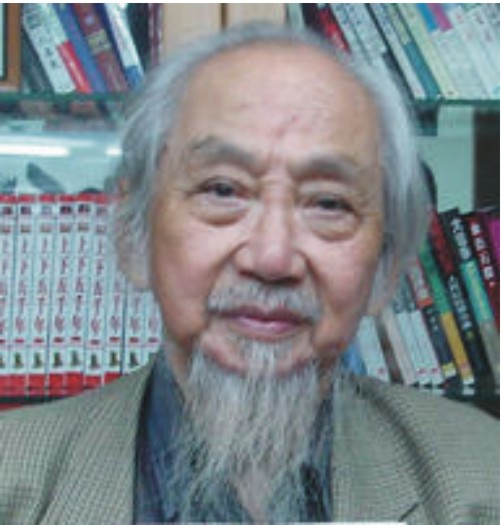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共评授了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还剩下290位了。”王秘书长对记者掐指算道。
摆在他眼前的,是由他牵头立项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调查报告》。这份于2008年12月完成的报告透露,在全部1865个工艺美术品种中,生存困难的536个,占28.74%;濒危的253个,占13.57%;停产的117个,占6.72%。这其中既有手工景泰蓝,也有天津“风筝魏”,它们都难以逃脱的困境是技艺后继乏人。
普查结果并未出乎王山的预料,他已经在工艺美术行业浸淫了20年,知道情况越来越变得“有些不妙”。
资金来了,大师去了
2月17日早上7时,王秘书长便领着十几号人,载着大大小小的摄像设备,冒着小雪出发了,目的地是河北省曲阳县。有人建议雪后天晴再去,但王山拒绝了,在他看来,“时间已经等不及了”。
只是车还未驶出北京,王山便接到电话:他们前往拍摄的对象卢进桥大师昨晚突然昏迷,凌晨已被送到北京救治。
为了拍摄这位全国石雕专业唯一的一位国家级大师,他们已整整等待了3年零7个月。2005年,王山接任秘书长不久,便意识到在世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们个个年事已高,便决定组织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对大师们的技艺进行抢救性拍摄,为后世留下一些影像资料,以防“人亡艺绝”。
卢进桥被确定为第一个拍摄对象。当年7月,开拍仪式在北戴河隆重举行,时年78岁的老人作为大师代表发了言,但此后他始终没能等到摄制组的到来。由于资金难以到位,专题片拍摄不得不搁置。2009年资金终于到位,拍摄工作才在2月17日重新启动。
接到电话后,王山决定先在曲阳拍摄完相关素材,第二天返回北京再到医院采访卢进桥本人。然而还没等他们赶到医院,大师已宣告不治。这次抢救性拍摄,尽管“事先连剧本都没来得及准备”,却仍然未能抢在时间前面。
资源少了,一些工艺品类濒危
与在世的大师一样越来越少的,是一些工艺品的原材料。
“大多数工艺美术原材料资源濒临枯竭。中国‘四大名石’之一的内蒙古巴林石已枯竭,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新疆和田玉、广东端砚石、河南独山玉储量稀少。”王山介绍道。
2006年,王山在新疆考察时,从一个工头口中得知,出产和田玉籽料的河床,已被沿岸2800多台挖掘机械挖掘过3遍,由于“东西越来越少,承包矿的租金也越来越便宜”。这个工头雇了10个工人,用两台挖掘机一大早便开工,一天下来,只挖出5块籽料,其中一块像瓜子大小,3块像食指指甲盖大小,还有一块像大拇指指甲盖大小。工头告诉他,“这还算战果不错的”,毕竟每公斤籽料的价格在40~80万元不等。
不少玉器厂领导也经常向王山抱怨,现在他们要做东西,得费很大的劲儿去找内线,才能淘到大块的籽料,而这些籽料多为一些家庭早年的囤积。
原材料的日渐匮乏致使一些玉器厂开始衰落。据王山介绍,一家在1980~1990年代非常红火的玉器厂,鼎盛时期职工人数达到2000多人,目前在厂里挂名的仅剩100多人,平时在岗只有80多人,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加工的不超过40人,并且大多在40岁以上。不仅如此,厂里的国家级大师们,在工厂已无太大的用武之地,只好在外面接私活。玉器厂的主要收入也并非来自玉器加工,而是来自工厂大楼的房屋租金。“说他们现在是房地产企业,或许更名副其实。”王山形容说。
从事牙雕的手工艺人的处境则更为艰难。由于象牙基本枯竭,绝大多数从业者不得不改行。坚守技艺的人们,则只能用牛骨等兽牙兽骨进行象牙风格的雕刻。只是在王山这样的业内人看来,这种工艺品的质地和光泽,“根本无法与象牙相比,味道全变了。”
因为学习过雕塑,王山对那种“味道”有着特殊的偏爱,“原汁原味的品味是不能替代的”。不过在他看来,与象牙雕刻这种工艺欣赏品不同,人们在家用陶瓷等工艺日用品上刻意追求的“味道”,则既浪费了自然资源,也给该工艺品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其实一个澡盆就要用很多高岭土,不要以为遍地都是用不完的高岭土。”这位秘书长忧虑地说。据悉,国家目前尚未出台限制高岭土开采使用的相关政策,前几年生产澡盆、瓷碗瓷盘大多使用最好的A类高岭土。如今,一些传统生产陶瓷的地方如唐山、淄博等地,都开始从外地买进高岭土。即便在以陶瓷闻名的景德镇,A类高岭土也已经很少,在生产日用品时,不得不像“棒子面掺白面”那样掺着使用。
“如果高岭土没了,那就意味着烧瓷大师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王山说。
眼看着不少大师身怀技艺而无施展之地,作为行业协会的秘书长,王山常常感到痛惜,而这也引发了他“摸清行业家底”的动机。最终的目的,则是根据“家底”,制订行业战略发展规划,“必要时呼吁政府给予支持和保护”。
“年轻人都不愿学,我们死后就没人会做了”
调查的结果,令王山心里有些沉重。在青藏高原,酥油雕塑因制作繁难,创作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年轻人,从而导致艺僧减少;在江苏无锡,曾深受世人欢迎的传统惠山泥人也已濒危;在四川,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成都漆艺和凉山州“彝族漆器髹饰技艺”早已陷入濒危状态……
贵州省大方县生产的皮胎漆器在日本很受欢迎,常被作为豪华奢侈的艺术品收藏,但在国内基本没有市场。在大方县的村里,王山和调查人员看到,只有一群老人在做这种漆器。带头的两个老人,一个65岁,一个70岁。
“年轻人都不愿学,我们死后就没人会做了。”老人说。
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秘书长侯惠哲,在苗寨看到的情形与此类似。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从事传统手工艺的,都是留守的中老年人或是背着孩子的女人。但一等孩子断奶,这些女人也将纷纷外出打工。多少年来,苗族的女子在出嫁前,会花大约一年半时间为自己织一件盛装,待出嫁那天穿。王山曾亲眼见识过一件这样的盛装,“简直美轮美奂”。但在苗寨,人们告诉侯惠哲,现在很少有人再为这样的盛装搭进去一年多时间了,“出嫁那天,买一件机器加工出来的穿上,就行了。”
即使在北京,情况也很不乐观。北京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滑树林在普查中调查完这里的民间工艺美术现状后,感到“问题较为严重”。2006年,厂里工人一度接近1500人的北京绢花厂宣布停产,剩下3000箱半成品需要处理。59岁的滑树林自掏腰包买下这些半成品,然后租来南三环一所中学教学楼的顶层,作为加工基地。
“不能让绢塑艺术就这么没了。”滑树林说。他曾是北京绢花厂的副厂长,1987年,他放弃副处级待遇,做绢人生意。20年后,他又重拾旧业。而他所谓的加工基地,人员不过是他加上4个徒弟。
根据协会的调查统计,绢人所属的品类,共有10个小类,发展良好的只有1个。“我就是这个‘1’。”滑树林指着统计表格里的“1”字说。
如今绢花和绢人在市场上已不多见。不过,在东花市大街一座大楼的地下室里,人们还可以集中看到。那是滑树林在东花市街道办事处支持下创办的绢塑艺术博物馆。他同时还为社区居民培训绢塑艺术。前来听课的,多是社区退休的老人。而他的4个徒弟,最年轻的也已经40岁了。
20年里,滑树林曾招过4个年轻徒弟,没一个能坚持下去,最短的学了一个星期就走了。
和滑树林一样感到无奈的,是中国最年轻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钟连盛。在工艺美术协会专门给大师发放的调查问卷里,钟连盛写下了“后继乏人”4个字。
他是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师,目前正带着3位年轻大学生为厂里设计景泰蓝产品。这家工厂在鼎盛时期有2000多个工人,目前还剩300多人,真正在生产一线的100多人。作为北京市的工业旅游示范点之一,常常有一车又一车的人来参观景泰蓝的生产流程。隔着玻璃,在车间里有条不紊工作的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也能见到三四个年轻人,但钟连盛介绍,那是从特殊教育学校工艺美术专业毕业不久的聋哑人。
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谈及一些工艺美术品类的“风雨飘摇”,不论是王山,还是滑树林,比较频繁地提到的两个词是“痛心”和“无能为力”。
在工艺美术品中,烟花爆竹行业因为需求较大,相对比较繁盛。但在王山眼里,“研发人才的缺乏”,随时可能给这个在低技术水平上徘徊的行业带来危机。他介绍,奥运会开幕式时用烟花打出的大脚印,其烟火造型技术,加拿大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研发出来。
作为培养人才重镇的工艺美术院校,曾经为国家的工艺美术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前后评授出的300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中,有70%或者从工艺美术院校毕业,或者在这些院校进修过。但随着全国院校合并或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专业调整,王山认为,大多数高等院校的工艺美术教学定位,不再注重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教学传授。即便是接受了传统工艺美术专业训练的大学生,就业时也大多转向了平面设计等方向。而从业的技艺人员大多对现代艺术了解不多,对传统技艺继承也不够,“有些不伦不类”。“学艺不从艺”现象日趋严重,这也加剧了高端人才的缺乏。高端人才的匮乏,又导致了稀有原材料的大量浪费。传统手工技艺通过“社会”进行传承的这条路,正越走越窄。
而通过“师徒”进行传承的这条路,也步履艰难。“聪明一点的需要学10年,耐得住相当长时间的寂寞,并且没有人能给予补偿。这对师徒都是考验。”副秘书长侯惠哲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无论是师傅还是徒弟,从经济和时间成本上,都很难熬过这个“修行”的过程。
当然,熬不过这个“修行”过程的,还有“家族传承”这种方式。在侯惠哲所调查的村寨,老人们告诉她,眼看着手工艺没有出路,儿女不愿继承父业,父母也就不再会要求子女学。
在王山看来,手工艺最主要的三种传承方式中,家族传承,断档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工艺美术的不少品类是‘十年不卖,一卖吃十年’,如果国家没政策,这些品类早晚得死。”王山称这并非“危言耸听”。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1997年5月颁布实施。但12年过去了,该《条例》实施细则始终没有出台。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负责起草的实施细则,早在十余年前便已提交当时的主管部门轻工业部,然而直到如今依旧没有得到批复。
“国家不能任传统手工艺自生自灭,不管哪一代人都得明白,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不是在沙滩上建的,而是在文化和传统上建起来的。”滑树林说。两年多来,为了让绢塑艺术进社区,他每周得从加工基地坐公交到东花市街道,讲3次课。
“我儿子有时候都觉得我有病,但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东西丢了。”滑树林如此解释自己的坚持。
钟连盛所在的珐琅厂,已经从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2002年改制之前,工厂连工艺美术学校的中专生都招不进来;改制之后,情况有所好转,陆续来了几个大学生。这位大师经常想到的也是传承问题。前辈大师把这门手艺传给了自己,“别在自己手里给断送了”。但钟连盛最近有些焦虑,因为他手下专业最出色的一名大学生,很可能将考上研究生离开工厂。
而在参加完卢进桥大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后,王山为了抢救性拍摄几乎马不停蹄。他说,再次看到报告里的数据,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