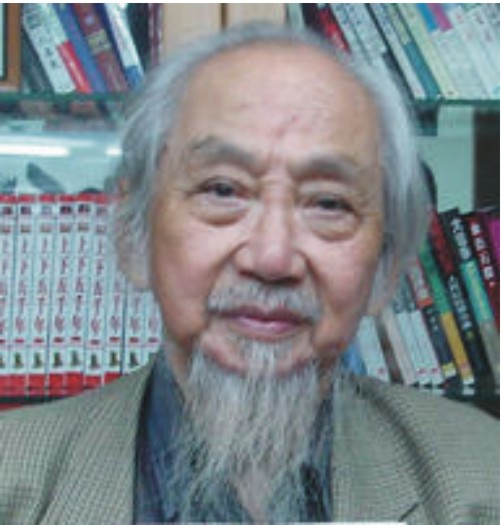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他应该寻找更温暖的价值归宿
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雷达 发布时间:2008-11-19 点击次数:
欲望化叙事
读陕西作家刘晓刚的《夜奴》,感觉与前年读他的《天雷》不大一样,我起初有些不得要领。读了几十页,除了看到大量欲望化描写,我几乎很难抓住作品的灵魂和意向。这可能与作品由八个中短篇连缀而成有关吧,但事情似乎又不止于此。我看问题在于它触碰到近年来一直在重复的一个命题:“欲望化叙事”。看来有必要对此做些清理了。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世俗生活成为一部分西方文学的歌颂对象,而世俗生活的标志之一便是欲望,但也只是肯定欲望的合理而已。有人说,自达尔文之后,上帝死了,无论是哲学思想界,还是文学艺术界,都以描写人的存在为主题,而人的存在因没有了永恒的上帝精神,便成为肉体化的欲望存在。欲望化叙事大体应该从那时肇始。自然主义便是那时的产物之一。曾几何时,欲望化叙事慢慢地简单化为性叙事或以性叙事为核心了。看近些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好像个个都是性叙事的能手。在中国,情形也不落后,可以追溯到横空出世的《金瓶梅》,它如彗星划过天际,但后来,成筐成堆的艳情小说就无法望其项背了。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来看,由于国家民族的路途曲折,五四后虽时有欲望化叙述的浮现,但真正的欲望化叙事高潮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情景与西方六七十年代弥漫的性革命有些仿佛。
但无论如何,与市场经济,消费化,娱乐化相伴随,我们来到了一个普遍的欲望化时代,而作为描述人类存在状态的文学便不可能没有与之相应的欲望化叙事。这也可以说是今天的文学一种必然表现。文学面对欲望,正视欲望,是势所必至,但问题在于怎样叙述,比如,欲望和人文理想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尖锐的、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欲望化叙事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城市文学和青春文学的流行,渐成时尚和气候,虽有一些较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不少作品完全顺从人的自然层面的欲求,与商品化对人的原始欲望的释放相互狂欢,以至用强度的刺激来娱乐人的身体世界,从而逃避对自我与世界的形而上关怀。有诗人甚至宣称,“即时消费”才是文学的最大意义所在,身体快感高于永远无解却又永远痛苦的精神拷问。
超越欲望
在刘晓刚的小说中,我之所以在长达几十页的描写中抓不住作品的要领,现在看来,并非文本的穿插和拼接所致,而是我漂行在欲望化的文字中。第一个故事《夜奴》能代表这种状态。小说一开始就渲染了一个欲望化的场面:主人公与一个不知名的性感美女的一场荒唐乐事。作者似乎是要拿这个故事来引导读者进入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故事:“朱良的故事”。然而,朱良的故事也只是一系列与性相关的场景组成。后面的故事大抵如此。在这八个故事中,我真正平静而深入地进入其间的是《昆湿奴的剑》。在我看来,这部中篇是所有中篇里写得最好的一部,是作者真正用心去写的故事。即使是中间的一些欲望化的描写,也是作者为了把八个故事有意连接起来的精心布局,也就是要把两个女主人公叶子和媛媛联系起来的那些描写。看起来,它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些多余成分,其实这些多余成分使八个故事有了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对欲望化的透视。
《昆湿奴的剑》使这部作品有了灵魂之美,有了较为深刻的意蕴。它的细节描写是成功的,能进入到人物灵魂,而其它故事,多在表层游走。虽然作者为我们描写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各种文化下的人物的形形色色,但是由于缺乏如《昆湿奴的剑》的纵深,所以整部作品广度大于深度。
这就为我们提出来另一个问题:欲望化叙事只能是表象的吗?它能否为我们建构一种超越欲望的精神道德价值?通俗一些说,文学能否为我们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寻找一些我们赖以存在的精神立场?
我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立刻有人说,文学不是载道的,文学没有这样的使命。这是现今一切流行文学的口号。其实,某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家虽反对文以载道,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道。只要落成文字,就会有意义,就有价值判断。这不仅是文字产生的原初意义,而且也是文字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与人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欲望沟通,而是文化符号上的沟通,沟通主要靠语言。于是,文学的“零度叙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要你写作,你就无法不表明自己的人生倾向和生活态度。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和平、幸福、共处的道德理想价值,而不是装聋作哑。即使是老庄的无为,也是为人类寻求和平幸福的一种处世之道。所谓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就是对当时价值混乱、道德崩坏的一种反拔。所以,我以为,即使在今天普遍的欲望化叙事背景下,修为崇高的大作家仍然会超越其时代限定和个体欲望,通过深刻而细节化的寓言,揭示人类存在的某些欲望化悲剧,追求终极价值,以此来警示我们存在的意义。
零度写作者?
有意思的是,因为《夜奴》,刘晓刚被定位为:零度写作者。我知道,定位者的意思是说他是个不带任何价值偏见或偏激感情的叙事者,即怎样发生就怎样去写。“零度”的提法,最早是在诗歌界,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标榜零度抒情,即不发表任何带有思想倾向的观点,不流露任何主体感情。虽然这不失为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和解共融的一条捷径,但我仍然怀疑这可能吗?事实上这恰恰是欲望化叙事的另一个特征。因为我们不对精神道德价值发表意见,就只能为欲望代言。或者也可以另图他途:在这种欲望化的叙事中,放弃旧的道德价值立场,寻找一种新的道德价值立场。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立场。
事实上,在刘晓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零度,而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苦苦寻找。那些生活在黑夜中的奴隶已经厌倦了欲望,他们在欲望中挣扎,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处处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爱、道德、友谊。在每一个故事中,被欲望左右的主人公在或快乐或麻木的性事之后,想到的首先是“爱情”二字。他们或仇杀,或忏悔,无非都是因为爱。这说明刘晓刚仍然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有确切的叙事倾向。作者告诉我们:“终于明白活了三十五年零五个月,我伤害最深的那个人是谁。我眼含热泪祈求那个人的原谅,那个人的宽恕和那个人的慈悲。那个人就是我。”“只要商人这个角色还能让我如此广泛地接触生活,如此深刻地探究人性,如此清醒地认知自我,我就会继续把这个角色演下去。”“我等待着转换角色的那一天。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但它必将来临。”
作者的自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用文学来拯救自我进而拯救人类的。我不知道将他定性为“零度写作高手”时他是怎样定位自己的,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定位对于真正视文学为“最高精神归宿”的他来说,是不大相符的。零度太冷了,不适宜人类生存。他应该寻找更温暖的价值归宿。
读陕西作家刘晓刚的《夜奴》,感觉与前年读他的《天雷》不大一样,我起初有些不得要领。读了几十页,除了看到大量欲望化描写,我几乎很难抓住作品的灵魂和意向。这可能与作品由八个中短篇连缀而成有关吧,但事情似乎又不止于此。我看问题在于它触碰到近年来一直在重复的一个命题:“欲望化叙事”。看来有必要对此做些清理了。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世俗生活成为一部分西方文学的歌颂对象,而世俗生活的标志之一便是欲望,但也只是肯定欲望的合理而已。有人说,自达尔文之后,上帝死了,无论是哲学思想界,还是文学艺术界,都以描写人的存在为主题,而人的存在因没有了永恒的上帝精神,便成为肉体化的欲望存在。欲望化叙事大体应该从那时肇始。自然主义便是那时的产物之一。曾几何时,欲望化叙事慢慢地简单化为性叙事或以性叙事为核心了。看近些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好像个个都是性叙事的能手。在中国,情形也不落后,可以追溯到横空出世的《金瓶梅》,它如彗星划过天际,但后来,成筐成堆的艳情小说就无法望其项背了。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来看,由于国家民族的路途曲折,五四后虽时有欲望化叙述的浮现,但真正的欲望化叙事高潮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情景与西方六七十年代弥漫的性革命有些仿佛。
但无论如何,与市场经济,消费化,娱乐化相伴随,我们来到了一个普遍的欲望化时代,而作为描述人类存在状态的文学便不可能没有与之相应的欲望化叙事。这也可以说是今天的文学一种必然表现。文学面对欲望,正视欲望,是势所必至,但问题在于怎样叙述,比如,欲望和人文理想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尖锐的、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欲望化叙事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城市文学和青春文学的流行,渐成时尚和气候,虽有一些较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不少作品完全顺从人的自然层面的欲求,与商品化对人的原始欲望的释放相互狂欢,以至用强度的刺激来娱乐人的身体世界,从而逃避对自我与世界的形而上关怀。有诗人甚至宣称,“即时消费”才是文学的最大意义所在,身体快感高于永远无解却又永远痛苦的精神拷问。
超越欲望
在刘晓刚的小说中,我之所以在长达几十页的描写中抓不住作品的要领,现在看来,并非文本的穿插和拼接所致,而是我漂行在欲望化的文字中。第一个故事《夜奴》能代表这种状态。小说一开始就渲染了一个欲望化的场面:主人公与一个不知名的性感美女的一场荒唐乐事。作者似乎是要拿这个故事来引导读者进入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故事:“朱良的故事”。然而,朱良的故事也只是一系列与性相关的场景组成。后面的故事大抵如此。在这八个故事中,我真正平静而深入地进入其间的是《昆湿奴的剑》。在我看来,这部中篇是所有中篇里写得最好的一部,是作者真正用心去写的故事。即使是中间的一些欲望化的描写,也是作者为了把八个故事有意连接起来的精心布局,也就是要把两个女主人公叶子和媛媛联系起来的那些描写。看起来,它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些多余成分,其实这些多余成分使八个故事有了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对欲望化的透视。
《昆湿奴的剑》使这部作品有了灵魂之美,有了较为深刻的意蕴。它的细节描写是成功的,能进入到人物灵魂,而其它故事,多在表层游走。虽然作者为我们描写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各种文化下的人物的形形色色,但是由于缺乏如《昆湿奴的剑》的纵深,所以整部作品广度大于深度。
这就为我们提出来另一个问题:欲望化叙事只能是表象的吗?它能否为我们建构一种超越欲望的精神道德价值?通俗一些说,文学能否为我们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寻找一些我们赖以存在的精神立场?
我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立刻有人说,文学不是载道的,文学没有这样的使命。这是现今一切流行文学的口号。其实,某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家虽反对文以载道,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道。只要落成文字,就会有意义,就有价值判断。这不仅是文字产生的原初意义,而且也是文字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与人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欲望沟通,而是文化符号上的沟通,沟通主要靠语言。于是,文学的“零度叙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要你写作,你就无法不表明自己的人生倾向和生活态度。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和平、幸福、共处的道德理想价值,而不是装聋作哑。即使是老庄的无为,也是为人类寻求和平幸福的一种处世之道。所谓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就是对当时价值混乱、道德崩坏的一种反拔。所以,我以为,即使在今天普遍的欲望化叙事背景下,修为崇高的大作家仍然会超越其时代限定和个体欲望,通过深刻而细节化的寓言,揭示人类存在的某些欲望化悲剧,追求终极价值,以此来警示我们存在的意义。
零度写作者?
有意思的是,因为《夜奴》,刘晓刚被定位为:零度写作者。我知道,定位者的意思是说他是个不带任何价值偏见或偏激感情的叙事者,即怎样发生就怎样去写。“零度”的提法,最早是在诗歌界,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标榜零度抒情,即不发表任何带有思想倾向的观点,不流露任何主体感情。虽然这不失为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和解共融的一条捷径,但我仍然怀疑这可能吗?事实上这恰恰是欲望化叙事的另一个特征。因为我们不对精神道德价值发表意见,就只能为欲望代言。或者也可以另图他途:在这种欲望化的叙事中,放弃旧的道德价值立场,寻找一种新的道德价值立场。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立场。
事实上,在刘晓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零度,而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苦苦寻找。那些生活在黑夜中的奴隶已经厌倦了欲望,他们在欲望中挣扎,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处处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爱、道德、友谊。在每一个故事中,被欲望左右的主人公在或快乐或麻木的性事之后,想到的首先是“爱情”二字。他们或仇杀,或忏悔,无非都是因为爱。这说明刘晓刚仍然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有确切的叙事倾向。作者告诉我们:“终于明白活了三十五年零五个月,我伤害最深的那个人是谁。我眼含热泪祈求那个人的原谅,那个人的宽恕和那个人的慈悲。那个人就是我。”“只要商人这个角色还能让我如此广泛地接触生活,如此深刻地探究人性,如此清醒地认知自我,我就会继续把这个角色演下去。”“我等待着转换角色的那一天。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但它必将来临。”
作者的自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用文学来拯救自我进而拯救人类的。我不知道将他定性为“零度写作高手”时他是怎样定位自己的,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定位对于真正视文学为“最高精神归宿”的他来说,是不大相符的。零度太冷了,不适宜人类生存。他应该寻找更温暖的价值归宿。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