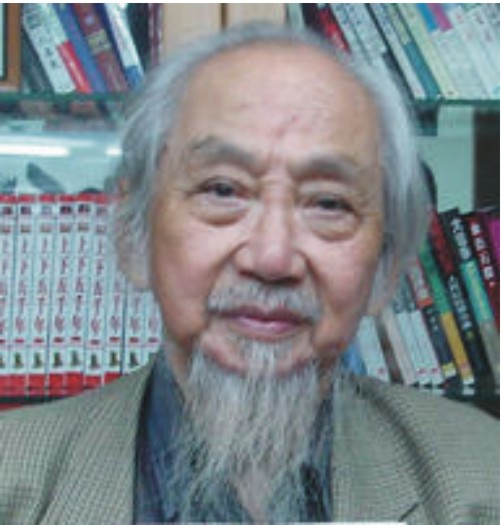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军旅诗歌:语词或思想的抛物线
作者: 来源:殷实 发布时间:2008-11-27 点击次数:
诗歌在近30年中的发展变化轨迹中,呈现为一个抛物线:“思想解放”之初的上世纪70年代末直至南线边境战争结束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呈快速上升趋势并达到顶点,之后则开始了不易觉察的回落或下降。这里所说的上升、顶点,主要是就军旅诗歌在由语言到情感继而思想的过程中所达致的某种和谐而言,也就是说,诗歌可以被认定为仍然是在“原初”的浑然状态下的抒情言志,诗人尚未放弃对公共生活、共同价值和民族感情等等的珍视。在后来的演进过程中,纯粹诗艺方面的拓展和精进并非没有,只是从整体看渐趋于“教条”式的僵硬和技术化的凌乱,尽管数目庞大,篇章可观,生气与活力却几近于无,诗意近于枯竭。
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逐渐形成了军旅诗概念的时期。之前人们知道有李瑛但不知有军旅诗,周涛这样的诗人一开始则是被划入了西部诗人、新边塞诗人的队伍。但是,当李松涛、程步涛、马合省、杜志民、贺东久、孙中明、孙泱、晓桦、刘立云、蔡椿芳等大批的诗人开始密集地发表作品,特别是以“战友诗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标志的一系列军旅诗歌集出版以后,军旅诗的存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从概念上都得到了确认,尽管是谁最先开始这样界定已无从稽考。这一时期的军旅诗有“带刺刀的爱神”、“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等一望而知的鲜明主题,也有“阵地上的小花”这样的准战争诗歌,晓桦的《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曾经让众多人为之侧目,退伍军人李钢的《蓝水兵》也名重一时,二者都获得过全国新诗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诗界备受推崇,一时多少后生竞相仿效。这一时期,诗人们的代言身份不辨自明,诗歌的言说和表达方式一律简朴明快,追求格言警句、营构巧妙形象蔚成风气,总体上都是在围绕着“军人意识”这一同时代的小说家们也非常重视的核心做环行运动。正是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努力,构成了整个上世纪80年代军旅诗歌的主体特征,歌唱着、吟咏着的诗人自身并没有多少突显自我的意识,而是将抒情主体控制在一个恰好可以被用来承载集体感受、集体美学分寸之内,因而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一种坦荡磊落的“大我”在出场。
上世纪80年代在大量的军旅诗写作中渐渐显现出自我与个性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位长诗写作者。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无疑最值得称道。在西部明净开阔甚至是荒凉的地域蛰伏已久的周涛,一进入南国的山岳丛林,就被一种地理上的强烈反差所震惊,所以他找到自然的重峦叠嶂和思绪的纷至沓来这种方式共同构筑自己词句的长城。在这部大型作品中,周涛制造了较之他所有诗歌的总和还要杂多的意象,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那里发生的战事在他的诗歌世界里一点儿也不局限于当时的浅表意义,他将对阵的双方视为拥有共同“祖母”(东方)的族亲,边境冲突不过是兄弟阋于墙。这正是周涛的过人之处,他本能地站在了人道和悲悯的一边而体察到普通士兵尴尬境遇、军人妻子哀伤悲愤,以及死亡引起的普遍的惊觫和感伤。“坟墓,把你里面的人还给我”这就是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关于那一场战争的诗歌作品还有很多,但是把战事所波及到的心灵灾难、大地苦痛表达到如此深厚者,惟周涛而已。
马合省至少有3首长诗《老墙》《苦难风流》《逃跑的马车》在当时是引人注目的。《老墙》写长城,《苦难风流》写红军长征,《逃跑的马车》写女英雄赵一曼。前两首写作之前,诗人曾分别沿长城和长征路线行走,以“今天”的近景切入,用历史的远景观照,尝试对“扶着墙行走的民族”和万里长征进行现代阐释。在《逃跑的马车》中,诗人面对早逝的女中豪杰,颖悟到的似乎是某种自美好和平享有者内心中生发出的罪感。
朱增泉是一个以爆发方式出现的诗人,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许多人一生都无法完成的诗歌总量。人们总是在意他的军阶、身份而小心翼翼地评价他的诗,实际上这样反倒是不够公平的。在上下求索的长诗《前夜》中,面对即将结束的世代和未知的新世纪,他声言:“祖国/我如芥的生命/负载着对你命运的忧虑和希冀”,这就是他自定的角色和天然立场。20世纪90年代前后,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东欧的变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怀疑与挫折,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地球腰腹地带”的动荡和战乱,使诗人不由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发问:“呵,你思想的海啸/难道真的会在20世纪之末/风静?/浪息?”显然这是一个无人能轻易驾驭的重大题材,而且此诗之后也确实再未见人有勇气作如是鸿篇巨制。朱增泉在冥思苦想中调校自己作为诗人又作为军人的双重视距,读者因此而得以窥见政治抒情诗的某种恢弘格局与气象。
被投射于诗歌世界中的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放任自我的时代。军旅诗人也开始转向——由代言公共感情而转向对个体意识的无节制挖掘、放大,由对自然山水、军营边关和历史文化等外在物象的观照,转向对枪械、弹丸、刀具之类“器物”的打量,自恋特点开始明显,世俗化趋势严重。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陡然增多,但语言粗糙随意,口语泛滥,节奏和韵律消失,诗歌的自律原则丧失殆尽。这一时期诗歌中无处不在的“自我”,事实上极大地歪曲了诗人的形象本身。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真正让我们尊敬的一位诗人是李瑛,提出这一点,一些骄傲的晚辈或许会感到有点意外和不屑,但我相信读过作品以后谁都会知道事实的确如此。《我的另一个祖国》是已近耄耋之年的李瑛在访问了贵州的贫困山区后含泪写下的作品:“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饥饿……”当诗人第一眼见到乌蒙山里的村野孩童时,他的心被重重地刺痛了:“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犹如史前部落的遗址”……这样的疑问,这样的良心的疼痛,正是我们久违了的真正诗人的感情。
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逐渐形成了军旅诗概念的时期。之前人们知道有李瑛但不知有军旅诗,周涛这样的诗人一开始则是被划入了西部诗人、新边塞诗人的队伍。但是,当李松涛、程步涛、马合省、杜志民、贺东久、孙中明、孙泱、晓桦、刘立云、蔡椿芳等大批的诗人开始密集地发表作品,特别是以“战友诗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标志的一系列军旅诗歌集出版以后,军旅诗的存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从概念上都得到了确认,尽管是谁最先开始这样界定已无从稽考。这一时期的军旅诗有“带刺刀的爱神”、“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等一望而知的鲜明主题,也有“阵地上的小花”这样的准战争诗歌,晓桦的《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曾经让众多人为之侧目,退伍军人李钢的《蓝水兵》也名重一时,二者都获得过全国新诗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诗界备受推崇,一时多少后生竞相仿效。这一时期,诗人们的代言身份不辨自明,诗歌的言说和表达方式一律简朴明快,追求格言警句、营构巧妙形象蔚成风气,总体上都是在围绕着“军人意识”这一同时代的小说家们也非常重视的核心做环行运动。正是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努力,构成了整个上世纪80年代军旅诗歌的主体特征,歌唱着、吟咏着的诗人自身并没有多少突显自我的意识,而是将抒情主体控制在一个恰好可以被用来承载集体感受、集体美学分寸之内,因而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一种坦荡磊落的“大我”在出场。
上世纪80年代在大量的军旅诗写作中渐渐显现出自我与个性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位长诗写作者。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无疑最值得称道。在西部明净开阔甚至是荒凉的地域蛰伏已久的周涛,一进入南国的山岳丛林,就被一种地理上的强烈反差所震惊,所以他找到自然的重峦叠嶂和思绪的纷至沓来这种方式共同构筑自己词句的长城。在这部大型作品中,周涛制造了较之他所有诗歌的总和还要杂多的意象,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那里发生的战事在他的诗歌世界里一点儿也不局限于当时的浅表意义,他将对阵的双方视为拥有共同“祖母”(东方)的族亲,边境冲突不过是兄弟阋于墙。这正是周涛的过人之处,他本能地站在了人道和悲悯的一边而体察到普通士兵尴尬境遇、军人妻子哀伤悲愤,以及死亡引起的普遍的惊觫和感伤。“坟墓,把你里面的人还给我”这就是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关于那一场战争的诗歌作品还有很多,但是把战事所波及到的心灵灾难、大地苦痛表达到如此深厚者,惟周涛而已。
马合省至少有3首长诗《老墙》《苦难风流》《逃跑的马车》在当时是引人注目的。《老墙》写长城,《苦难风流》写红军长征,《逃跑的马车》写女英雄赵一曼。前两首写作之前,诗人曾分别沿长城和长征路线行走,以“今天”的近景切入,用历史的远景观照,尝试对“扶着墙行走的民族”和万里长征进行现代阐释。在《逃跑的马车》中,诗人面对早逝的女中豪杰,颖悟到的似乎是某种自美好和平享有者内心中生发出的罪感。
朱增泉是一个以爆发方式出现的诗人,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许多人一生都无法完成的诗歌总量。人们总是在意他的军阶、身份而小心翼翼地评价他的诗,实际上这样反倒是不够公平的。在上下求索的长诗《前夜》中,面对即将结束的世代和未知的新世纪,他声言:“祖国/我如芥的生命/负载着对你命运的忧虑和希冀”,这就是他自定的角色和天然立场。20世纪90年代前后,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东欧的变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怀疑与挫折,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地球腰腹地带”的动荡和战乱,使诗人不由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发问:“呵,你思想的海啸/难道真的会在20世纪之末/风静?/浪息?”显然这是一个无人能轻易驾驭的重大题材,而且此诗之后也确实再未见人有勇气作如是鸿篇巨制。朱增泉在冥思苦想中调校自己作为诗人又作为军人的双重视距,读者因此而得以窥见政治抒情诗的某种恢弘格局与气象。
被投射于诗歌世界中的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放任自我的时代。军旅诗人也开始转向——由代言公共感情而转向对个体意识的无节制挖掘、放大,由对自然山水、军营边关和历史文化等外在物象的观照,转向对枪械、弹丸、刀具之类“器物”的打量,自恋特点开始明显,世俗化趋势严重。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陡然增多,但语言粗糙随意,口语泛滥,节奏和韵律消失,诗歌的自律原则丧失殆尽。这一时期诗歌中无处不在的“自我”,事实上极大地歪曲了诗人的形象本身。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真正让我们尊敬的一位诗人是李瑛,提出这一点,一些骄傲的晚辈或许会感到有点意外和不屑,但我相信读过作品以后谁都会知道事实的确如此。《我的另一个祖国》是已近耄耋之年的李瑛在访问了贵州的贫困山区后含泪写下的作品:“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饥饿……”当诗人第一眼见到乌蒙山里的村野孩童时,他的心被重重地刺痛了:“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犹如史前部落的遗址”……这样的疑问,这样的良心的疼痛,正是我们久违了的真正诗人的感情。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