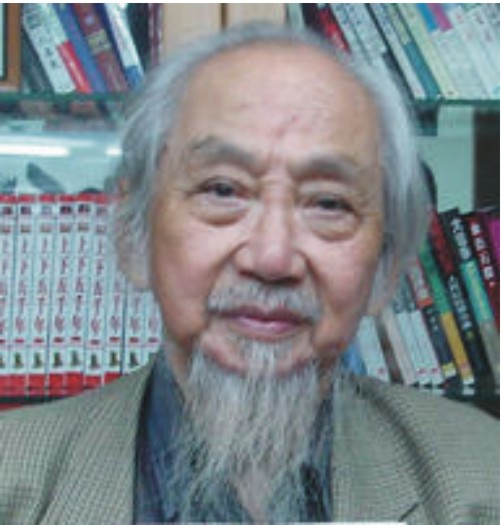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陈晓明:我的阅读野史与治学归宿
作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陈晓明 发布时间:2008-12-8 点击次数:
●汇集陈晓明近20年代表文章的《审美的激变》一书,将于2009年在作家出版社推出。回望走过的学术道路,陈晓明心生感慨,特为本报撰文,谈及其阅读历程和由此而生的治学归宿。
●“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
现在是图像统治的时代,看看青少年在网上网下读图,影像、声像、动漫、声光电……再在耳朵上别个MP3,这几乎就是文化的全部内容了。大家都知道这并非好兆头,但谁都无能无力。这是与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工业时代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播方式,谁能抵抗这样的时代潮流?想想还是在战后的50年代,已经落寞的海德格尔那么严厉批判科学技术,谁能解其中深意呢?现在就是解了,又有什么用呢?惟一对电子工业略微保持一点距离的人,会对阅读表示一种留念。一说阅读,我们那个时代的贫乏的阅读,那么可笑,又那么珍贵。
我早年喜好理论,“早年”到什么地步?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那年我11岁。我从10岁跟随父母下放到非常偏避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马列著作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捧着这本书,爱不释手。书名是在多年后才搞明白,一直不知道杜林是一个人名。以为“反杜林”是某件事情、某种行为。但那时,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本书是白色的封面,印上红字,还有红的细边框。怎么看,都觉得那里面有太多的奥秘。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后来还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什么也没有读懂。我12岁就会砍柴劈柴,会破篾。因为点煤油太奢侈,就点燃篾片照明,破篾很挑战技巧的,但并没有难倒我,我那时就有比较强的劳动自信。不过每次看到《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就很沮丧,觉得自己要进入这个世界还有一定差距,也可能决心在那时就下了。
那个年代,我身处偏僻山区,那里连电灯都没有,更不用说图书。回想起来,阅读报纸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最大的收获,那时读《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快乐。我从11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11岁一直读到17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后来问我的硕士生导师李联明教授,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他说《参考消息》,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也是读《参考消息》起家的。就冲这一点,他以为孺子可教。《参考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可视的窗口,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存在。
当然,我们那时没有数理化的困扰,复课闹革命也主要是学工学农。这使我们有时间去读文学名著。说起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拜伦,文学名著在17岁以前读了不少。那些现在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差不多都在那时解决了。但中国古典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东周列国传》;“红色经典”中我最喜欢的是《小城春秋》;外国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傲慢与偏见》。
后来读中文系,最早读的理论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当然,另一方面,别车杜一度是我的偶像,几乎是伟大的导师。俄罗斯文学也是我的酷爱,那是一种非常深广的文学。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说。直到袁可嘉编的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那等于杀了我。
后来,也就是在1980年,有幸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所读到的武侠小说里说的一样,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或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那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实际上,如有闲谈,超过五分钟我就着急了。现在如有人和我打电话,如果不是谈正事,闲扯超过五分钟,那也是对我的忍耐性的折磨。不因别的,早年落下的毛病。
实际上,我书读得很杂、很野,也很粗。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因为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在等着我,那时就知道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读得较细的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是我钟爱的一本书,连他的生平事迹都让我钦佩不已。这个人年轻时特别保守平和,据传记作家说,罗素在55岁后变得有些激烈了,80岁还和他的女秘书结婚,88岁还在伦敦大街上禁坐,活了98岁(1872-1970)。那时觉得西方的知识分子真是一种“传奇”啊!现在的人肯定不以为然。
这就是80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读的是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虽然与我的理论趣味相关,但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肯定不能这么读书,他们被学分和考试搞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文学),把当代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的原因,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早年喜好哲学和理论时,觉得做当代文学或说文学评论实乃雕虫小技,那时有朋友劝我做当代评论,但我不为所动,看着那些做当代的人早早成了名,很不以为然,那不就是浪得虚名吗?当代的那些作家,哪有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有质量?但后来做了当代,开始不过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但一做就收不了手,这就陷进去了……我也就这样搞起了当代,不知是不是变成自己的专业。岁月如流,一晃就是20多年,转眼就50岁,所谓知天命,就是该死心了。
其实做起了当代文学,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
这就是我在学理上的初衷了。现在想想,我在80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强大的历史压制,强大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80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看看我在80年代初期写的文章,诸如《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80年代后期的那些理论批评,总有“立”在其中。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过去,这就是有效的破。我以为小打小闹的揪辫子,打棍子,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没有立在其中。有“立”的蓝图,那些陈旧的东西必然消失。
我们当年阅读西方的书,其实是想找思想和方法;现在读西方的书,则只是找些知识材料。我们那时读到兴处,那是眼前的豁亮,所谓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尽管我们那时读西学不时遭遇到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的质疑;现在则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合法性问题。阅读在中国还总是遭遇到“身份政治正确”的困扰,如果写成文章,这样的困扰更甚。只是我们这些从煤油灯下开始读书的人,从《反杜林论》读起来的人,从一张报纸开始读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只有阅读,阅读本身就构成了阅读全部的合法性,有阅读,就有快乐,就是至福。
●“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
现在是图像统治的时代,看看青少年在网上网下读图,影像、声像、动漫、声光电……再在耳朵上别个MP3,这几乎就是文化的全部内容了。大家都知道这并非好兆头,但谁都无能无力。这是与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工业时代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播方式,谁能抵抗这样的时代潮流?想想还是在战后的50年代,已经落寞的海德格尔那么严厉批判科学技术,谁能解其中深意呢?现在就是解了,又有什么用呢?惟一对电子工业略微保持一点距离的人,会对阅读表示一种留念。一说阅读,我们那个时代的贫乏的阅读,那么可笑,又那么珍贵。
我早年喜好理论,“早年”到什么地步?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那年我11岁。我从10岁跟随父母下放到非常偏避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马列著作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捧着这本书,爱不释手。书名是在多年后才搞明白,一直不知道杜林是一个人名。以为“反杜林”是某件事情、某种行为。但那时,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本书是白色的封面,印上红字,还有红的细边框。怎么看,都觉得那里面有太多的奥秘。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后来还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什么也没有读懂。我12岁就会砍柴劈柴,会破篾。因为点煤油太奢侈,就点燃篾片照明,破篾很挑战技巧的,但并没有难倒我,我那时就有比较强的劳动自信。不过每次看到《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就很沮丧,觉得自己要进入这个世界还有一定差距,也可能决心在那时就下了。
那个年代,我身处偏僻山区,那里连电灯都没有,更不用说图书。回想起来,阅读报纸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最大的收获,那时读《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快乐。我从11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11岁一直读到17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后来问我的硕士生导师李联明教授,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他说《参考消息》,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也是读《参考消息》起家的。就冲这一点,他以为孺子可教。《参考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可视的窗口,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存在。
当然,我们那时没有数理化的困扰,复课闹革命也主要是学工学农。这使我们有时间去读文学名著。说起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拜伦,文学名著在17岁以前读了不少。那些现在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差不多都在那时解决了。但中国古典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东周列国传》;“红色经典”中我最喜欢的是《小城春秋》;外国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傲慢与偏见》。
后来读中文系,最早读的理论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当然,另一方面,别车杜一度是我的偶像,几乎是伟大的导师。俄罗斯文学也是我的酷爱,那是一种非常深广的文学。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说。直到袁可嘉编的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那等于杀了我。
后来,也就是在1980年,有幸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所读到的武侠小说里说的一样,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或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那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实际上,如有闲谈,超过五分钟我就着急了。现在如有人和我打电话,如果不是谈正事,闲扯超过五分钟,那也是对我的忍耐性的折磨。不因别的,早年落下的毛病。
实际上,我书读得很杂、很野,也很粗。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因为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在等着我,那时就知道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读得较细的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是我钟爱的一本书,连他的生平事迹都让我钦佩不已。这个人年轻时特别保守平和,据传记作家说,罗素在55岁后变得有些激烈了,80岁还和他的女秘书结婚,88岁还在伦敦大街上禁坐,活了98岁(1872-1970)。那时觉得西方的知识分子真是一种“传奇”啊!现在的人肯定不以为然。
这就是80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读的是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虽然与我的理论趣味相关,但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肯定不能这么读书,他们被学分和考试搞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文学),把当代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的原因,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早年喜好哲学和理论时,觉得做当代文学或说文学评论实乃雕虫小技,那时有朋友劝我做当代评论,但我不为所动,看着那些做当代的人早早成了名,很不以为然,那不就是浪得虚名吗?当代的那些作家,哪有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有质量?但后来做了当代,开始不过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但一做就收不了手,这就陷进去了……我也就这样搞起了当代,不知是不是变成自己的专业。岁月如流,一晃就是20多年,转眼就50岁,所谓知天命,就是该死心了。
其实做起了当代文学,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
这就是我在学理上的初衷了。现在想想,我在80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强大的历史压制,强大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80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看看我在80年代初期写的文章,诸如《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80年代后期的那些理论批评,总有“立”在其中。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过去,这就是有效的破。我以为小打小闹的揪辫子,打棍子,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没有立在其中。有“立”的蓝图,那些陈旧的东西必然消失。
我们当年阅读西方的书,其实是想找思想和方法;现在读西方的书,则只是找些知识材料。我们那时读到兴处,那是眼前的豁亮,所谓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尽管我们那时读西学不时遭遇到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的质疑;现在则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合法性问题。阅读在中国还总是遭遇到“身份政治正确”的困扰,如果写成文章,这样的困扰更甚。只是我们这些从煤油灯下开始读书的人,从《反杜林论》读起来的人,从一张报纸开始读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只有阅读,阅读本身就构成了阅读全部的合法性,有阅读,就有快乐,就是至福。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