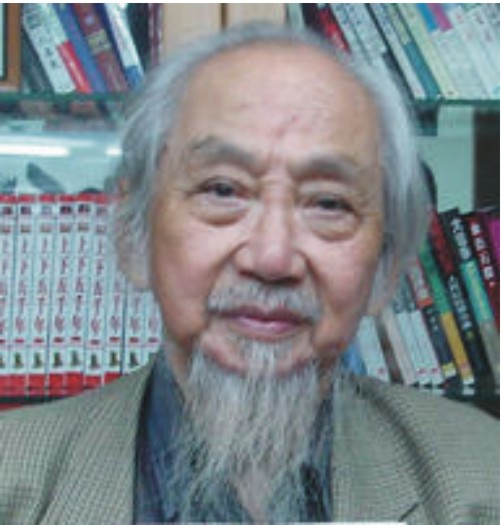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8-12-17 点击次数:
| 新时期发轫期,女作家们在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究中,渐次进入性别领域,女性意识得以苏醒,女性感觉得以发育,女性特征得以复位。她们在对爱的权力、信念的追逐中,证实了“爱”对于女性生命的基础性意义;她们在对真、善、美和温柔的宣扬里,纠正了以往不谈性别差异的平等论以及无性化情状。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终于获取了实质性的结合。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作家女性意识不断地增涨,女性文学颇成气候,一道亮丽的女性文学风景线终于横空出世,照亮于文坛。张洁、舒婷、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不胫而走,其所呈露的女性尊严、怀疑精神乃至性意识,震撼着文坛与读者。从《方舟》到《玫瑰门》,无不让人或感动、或惊诧、或不安、或责难,它们为人们所带来的动静至今尚未止息,所带来的气息至今依然缭绕。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标志性岁月。女作家们不仅度过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的狂欢节,她们的创作也进入到空前的高潮期、丰收期。假如说,“五四”女性文学是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现代性转型的话,那么,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则为又一轮转型——向多元化的转型。今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交织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女性主义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都在催使中国女性文学作出转型性反应;本轮转型现正处于进行态,既深刻又全面。这轮转型不仅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还回答了之前某些男士所忧虑的“女性主义文学能走多远”的疑虑。我以为,中国女性文学正依据自己所开创的性别和超性别相融会、相整合的思路和视界,继续勇敢地向前迈进。路上,肯定依然会遭遇到他设和自造的麻烦、曲折,甚至陷阱;但,路,一定会越走越阔广,越走越深远。 由改革开放初始作好准备,世纪之交以来正式启动的女性文学转型,就女作家的性别立场和视界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张洁为始,翟永明、陈染、林白为续,徐坤等探索和实践为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视野。其二,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范小青、王小妮等为代表,虽具深厚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性也时有表现,但却坚持追逐、探索超性别的立场与视野。其三,迟子建最先提出了文学的性别和谐论,主张消解男女之间内在紧张,致使世界不至于倾斜而丧失平衡。诚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无严格界限,何况各类型内部常有自我消解和矛盾情况,各类型之间的观念也常有交叉和变化,此等划分,仅为研究方便而为,绝非科学论断。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却在于她们的趋同方面。随着女作家各自成长轨迹的清晰呈露,我们发现:一,新时期初始,女作家们强化女性意识的要求与实践,是具有很强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的;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强调,正是对女性主体人性的强调,其为女性话语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上世纪90年代,反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抬头,以女性个体经验为核心的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一时试图取代宏大叙事和集体经验的话语;但较快地,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广大女作家,包括以往较沉溺于自恋的女作家,也都不再将性别元素孤立、封闭起来,她们竭力地将性别意识、视角,同国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视角整合一体,置性别元素于各相关文化结构之中。她们似乎不再专注于女性主义称谓(原先专注于这个称谓的,也绝非多数),而要将个性主义、人性主义作为自己最真切的追求目标了。三,面对繁复的性别歧视(以市场经济主宰的性别歧视为最突出)现象,女作家们依然不放弃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然而,基于对人性结构深入的透视和理解,她们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一方面感到不宜搞绝对化的性别主义,一方面则追求和谐关系的建构。既然性别关系的基本内核属人性关系,那么,就应在彼此尊重各自主体人性的基础上,协调好“主体间性”关系。即,双方应互为主体、彼此对话、互助互动,以求男女共生、和谐共存。对共生共存男女关系的追求,反映在创作视界上,正是性别与超性别的交汇和融合之境。 从张洁到徐坤,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们,她们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上的表现,是30年来女性文学演变的重要征兆与象征。 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刻,还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寻找男人的意味;但从《方舟》到《只有一个太阳》,再到《无字》时,她却已是个相当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了。当她撕开男人人性面具、逼近男人人格真实的时候,那种捅破自己制造的乌托邦神话的反思、忏悔劲头,令人震撼;那种失望于男人、尤其男人“精英”,无情地撕破其自私、虚伪、轻浮、庸俗、不负责任等真相时的决绝态度、愤懑神情,更令人敬畏。然而,张洁至今仍然不愿被人归纳到“女权主义”中去,她认为,这样做只能是“画地为牢”(参见钟红对张洁的采访,《文汇报》2006年2月27日),会限制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张洁创作尽管有自己的年轮和转型,但其同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制度的关联,却始终如一。《无字》同中国百年变革历史的纠缠,呈现得何等生动和深刻!张洁正是因她的既性别又超性别的立场和视野,才成就了她杰出的文学业绩。 翟永明抒写《女人》组诗时,那种顽强抵抗和拆解“野蛮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的执傲劲,热切期待女性伟大原生力、原创力焕发的激情流,至今还在激动着我们;而她那“穿黑裙的女人”和“黑夜意识”,也终于成为了女性诗歌的经典性符号。然而,翟永明很快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标准》创刊号)的问题。她一方面继续着女性题材创作(如大型组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倾心于女性家族史的谱写;一方面却沉溺于有关自由、美和艺术等命题的开拓了。她开起了“白夜酒吧”,周游世界,一方面继续着“出自女性之喉”的表达,一方面却探索起“双性沟通对话乃至双性同体式的吟述”(陈超语)了。翟永明犀利的性别洞察力和不断成熟的女性意识,使她原先“自白式”诗句所呈露的狂热激情有所降温,但那个体生存体验与时代生存本质的联系却更其紧密;诗作的人类性和生命意味剧增,诗歌的技艺也更其精湛。为之,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07年10月授予她“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据说,授奖词赞扬她的诗作“能量充沛,情境深邃,肌理细腻,意味幽怨”。 刘索拉、陈染也都不隐讳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而今,她俩一个提出女人应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刘索拉、西云《刘索拉:我的女性主义和女性味》,《艺术评论》2007年3期),一个则明确表示“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林宋瑜《陈染:破开?抑或和解?》,《艺术评论》2007年3期)。刘索拉以为,“人没有必要保持绝对女性和绝对男性的状态,那种状态其实很愚蠢”,因为“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一大因素就是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人应在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引导下,“感知自然的双性,并顺其自然的双性”。她觉得自己正是个能感悟双性的幸运儿,这样,既写出了兼具女性特色和历史大场面的小说《女贞汤》,又谱成了揭示女性心理阴暗面的新歌剧《惊梦》,作品的视野都是双性的,对女性自我所持有的阴暗与弱点也都不予避讳。陈染一贯以女性性别引以为“美好和荣耀”。但她长于哲思的思维方式,让她认可伍尔芙关于“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观点。以往,人们在短论《超性别写作与我的创作》、小说《破开》《私人生活》中,一方面发现了她对姊妹情谊、女同性恋的倾心,另一方面却注意到,她希冀男女精神结合以求人格完整的心愿。陈染认为,认识和欣赏一个人,假如拘泥于性别的话,那就“未免肤浅。”应该说,她是较早具超性别意识的。晚近,在反思自己青春期锋芒的时候,她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内敛起来”,深埋“反骨”;一方面却坚持女作家应“把男性和女性的优秀品质融合起来”,以求作品“感情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说:“我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作为人性主义者的陈染,她的性别和超性别自有其独特的方面。她以包容、开阔胸怀,理解和感受人性的丰富性,包括对女同性恋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她以哲人的睿智,思考男人与女人的长短,并着力扬弃自已身上的人性弱点,以求继续“成长”。 林白,一直认为创作由生命深处而生,是个人的言说,因而更倾心于个人主义;然而,当大家把她列入女性主义时,她也不反感,并认可了自己“算得上”是个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作家”。2003年,她的长篇《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获得成功,《妇女闲聊录》还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是她的黄河之行、深入湖北农村以及同从农村请来的“女管家”亲戚作了深入交谈之后的结果;是她从房间、从窃窃私语中走将出来后,由蓝天和大地给予她的回报。她感慨道,写《妇女闲聊录》时有一种“回到了大地”,以及大地给了自己“温暖”的感觉。她甚至提出,是这种“低于大地的姿势”,使自己“找到了文学的源头”(林白《世界如此辽阔》,《前世的黄金——我的人生笔记》第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林白的感受,意味深长,难怪她要说自己的创作“远不止女性文学这一块”。 徐坤,这位我曾称之为女性文学“吉祥鸟”的实力派作家,自走上文坛以来,或以反串、易性写作,操持着对知识界虚伪自私之境的炮轰,或以女性身影正面袭击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权立场清晰而顽强。她知道,男权意识充斥于世的今天,男权话语形态覆盖于文坛的时候,女作家倘若选择不好视角,就难以呈现女性自己的身姿和发出自己的声音。1996年,她严正提出“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其所肩负的任务则为:一“反抗”,二“自我发现”。这里,她“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鲜明而突出(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0日),其态度和言辞,果然被人称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宣言”。然而,她渐渐地感悟到,两性关系毕竟属于“共存”关系,一味地“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得安宁”(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近些年来,她真的不再只取一端,或装扮成男人看女性,或执著于女人视点看男性,而试着男女“对看”(万燕《从徐坤看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的前途》,《女性的精神》第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了。人性的“主体间性”,除了“对话”,还须“对看”;只有努力地认识对方,才能真切地对话和沟通。从她几部长篇新作如《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来看,徐坤已明白了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的重要性,明白了作家在人与人之间搭筑起心灵桥梁的责任。这些作品无论宏观切入,还是微观透视,都非常到位,尤其在挖掘人物内心真实方面,相当出彩。自徐坤潜入人物内心,把握住人的最真实所在的时候,她终于让男人和女人之间既对看、又对话,既沟通又理解了,她的创造性也由此而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王安忆、铁凝们对超性别视野的探索,同张洁、徐坤们的探索有许多相叠之处,尤其在女性主义的自审方面就相当一致。王安忆和铁凝们对男性生存的艰难都予以同情,对女性自我的认可都觉得不宜过于自赏和自恋。因而,她们对男权中心话语的批判、颠覆性意象呈现了逐渐淡化的趋势;而对女性自我中负面性的解构则有所增多。当然,这里的超性别,不等于男性化,也不等于背离自己性别。超性别是自我性别的升华,是更加人性化性别的呈现。女作家对女性负面和男性负面批判中所表露出来的母性关怀,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方方《万箭穿心》中女主人公粗俗、愚昧而无知,让人难以忍受,但作家对她的悲悯,却让人看到了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抗住”的内在的大善和大爱。叶弥《小男人》中那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小男人,作家同样以母性意识予以关照,让那令人作呕的负面,由人性的脆弱面得以披露,留给了他些微的尊严。探索超性别的女作家们,大多存有饱满的母性意识,她们的“超”除了同宏观世界联接外,更在于人性的提升。性别对抗少了,人性关怀多了。 铁凝提出的“第三性”视角,则是探索超性别一派的最大亮点。铁凝早在《玫瑰门》“写在卷首”中提出了“第三性”视角;《笨花》出版时,她再度提到了它,并称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种“超越感”。铁凝一直认为“人性结构的丰富性给文学带来了说不尽的视角”,该说法正是第三性视角的最好注释。不是吗?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繁复的人性世界,恰恰是这个能“生万物”的第三性视角才可能抵达的吧。“三”这个数字,太值得研究了。历史学家庞朴曾研究过“三”的秘密。他认为,中国古代十分看重“三”这个数字,因为“数始于一,终於十,成於三”;“三”字是“天参”,“天”参与的数;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八卦由三画组成,太极元气是“函三为一”(即三位一体);创作的超越,也将是“成於三”啊。庞朴提示我们,人应当了解“三”的秘密,以从二分世界中解放出来。铁凝这个“第三性”提法,也许正是性别和超性别融合之路的重要通道? 迟子建作品,有一种传神的魅力和魅性,那里,洋溢着爱和温暖。她把故乡和大自然看作自己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她对待笔下的男人和女人,像对待自己亲人和兄弟姐妹一样,一片诗意,一片温馨。她很像冰心,总想用爱温柔这个世界。有人提醒她,如此温情会阻遏了对人性恶的更深层的探究和揭示,但她却表示:对恶和残忍的表达要节制,对温暖却是不需节制的。她总认为,作家理应去采摘那锁在人的心底深处的蜜,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开阔、神圣和高尚。女作家的观念,常常以其人生体验进行表达,迟子建的性别观除了谈及和谐论外,她更以自己的作品直接宣扬她的天人合一论和男女与共论。迟子建不喜欢给笔下男人和女人“定型”,落入同一模式;但她却坚持自己的质朴和温暖气息,愿以这种气息使男人和女人得到幸福,尽管这是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迟子建的和谐论、温暖情,使她的性别和超性别的融合之路越走越开阔,越走越灿烂。 |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