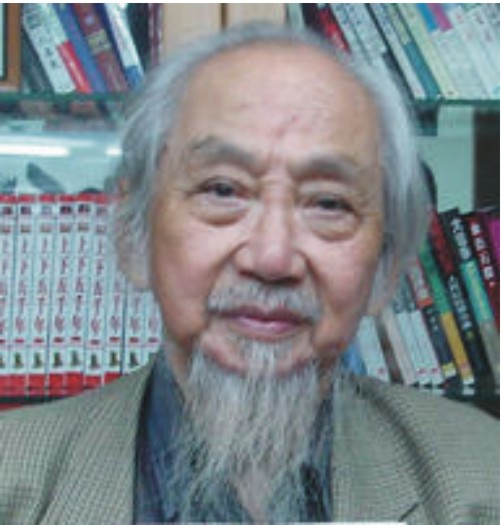1980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和文学路向。198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年《收获》的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震动文学界。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作家集体亮相。
事实上,“先锋作品专号”并非先锋文学的发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同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才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开拓之作。他在1985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当时文学青年推崇的文本,后来毕飞宇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也说:“马原是我的老师。”不过,因为1987年《收获》的这个专号的推出,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
“先锋作品专号”的推手是年轻编辑程永新,他的建议得到了李小林和编辑部的支持。“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代作家不同。”程永新后来回忆说,“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马原都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散兵游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做这事难度非常大,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程永新当年力推的这批作家1990年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成了他20多年的老朋友。
“先锋作品专号”中的不少作品令老一辈作家头痛不已,有老作家直言一篇也看不懂。直到1988年第六期,《收获》才再次推出“先锋作品专号”,收入作品有《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不过,其气势明显不如第一期,多数作家也已是《收获》和文坛的老面孔了。用马原对早报记者的话说,“颓态渐露。”
马原 叙事革命代表
专号上当时最大牌的作家是马原。实际上早在1985年,马原就已经在《收获》上开始发表作品,《西海的无帆船》刊登于1985年的第五期上。“《西海的无帆船》是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想要在《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求太高了。在发表《西海的无帆船》之前,我已经给《收获》寄过稿子,不过都被退回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西海的无帆船》写于1984年,那时的马原还是在西藏工作的记者。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他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许多人模仿和小说实验的起点。与此同时莫言则在表达自己的感觉方面显示其先锋性。1982年,马原来到西藏工作,“在我来到西藏后写的第一期小说中,大多具有强烈印象式的风格,但随着我对西藏的慢慢了解,第二期的小说开始关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西海的无帆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西藏有很多无人区,无人区里生存的困难特别适合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西海的无帆船》,坦率地讲,小说里有我个人经历的成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
而发表在专号上的《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人经常开玩笑说1987年是‘马原年’,因为除了《收获》,那年我还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重要作品。1987年是我写作状态最好,作品写得最多、发得最多的一年,但当时文学上的繁荣,在我个人看来已经透出了一点颓势,我的个人写作也出现了颓势,这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得到了印证,而我在1989年之后写作基本上就中断了。也正因为如此,李小林大姐好几次都鼓励我再次写作,她常常说:‘别人不写我不管,但马原你不写我要管。读者那么喜欢你的作品,我们那么喜欢你,你说不写就不写了?’”
先锋的马原在创作了让他近乎虚脱的《上下都很平坦》之后,最早走上“平坦”之路,然后慢慢不再写作。
余华 道·琼斯指数
1987年专号的最大得益者之一无疑是余华,此前他仅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过一两个短篇。先是《四月三日事件》上了专号,然后在紧接着的第六期,《一九八六》又上版了。在《四月三日事件》里,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着自己在说“四月三日”,因而以为四月三日将有一个阴谋针对自己发生。当“他”试图去弄清楚四月三日究竟有何不寻常时,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他的问题并监视着他,这使他确信他们都是“四月三日事件”的同谋者,终于在四月三日来临之际爬上一列运煤车离家出逃。这样,作为幻觉的迫害不论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对于自我来说,它已经以出逃和无家可归的结果成为真实存在。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作家之一,“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三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余华对早报记者说,“在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之后,1987年第六期上又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当时我的编辑是肖元敏,他认为这部小说中一些残酷的情节描写在当时不太能被接受,他希望我做些删节。肖元敏为了此事,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我做些修改,并手抄全文附上了他的修改意见。我非常感动和受宠若惊,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名无名作家,编辑对无名作者作品胡乱修改是常有的事情。”
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的,“李小林看到后,她就坦率地对我说,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不好,要求我修改,直到她满意了才行。她这么严厉可能是她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作家,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于是,我几乎把后半部分重新写了一遍,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在余华看来,“《收获》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琼斯指数,从《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所以,肯定有爆发,有平庸。”
莫言 来自49年以前
莫言没有赶上“先锋号”。1985年,第五期《收获》发表了莫言的《球状闪电》,“《球状闪电》是我1984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写的,写完后给了同学崔京生,他跟《收获》有点关系,趁着1985年初春节探亲的机会带到了杂志社,没想到在1985年第五期上就发表了,我记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二条位置。”莫言对早报记者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幻想常常和写实成分交叉并进,混合交融,使作品具有一种亦幻亦真、朦胧迷离的特色,如《球状闪电》。从《球状闪电》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后来被称为“先锋”的作家们是如此地深受拉美文学的影响,比如在《球状闪电》中,鸟老头大把大把地吃墙上的蜗牛及腐土里的红蚯蚓的情节,就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丽贝卡吃蚯蚓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中,莫言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是1987年的《红蝗》,“《红蝗》写得过于渲染了,当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稍微节制点,当时没有那么做,有点遗憾。”在《红蝗》中,莫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丑的上面,一种对丑的堆砌。他恨不得把所有被人们认为是丑的东西在这里都写到,诸如屎尿、尸体、污垢、伤口、死亡等。
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之多,“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莫言说。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观念的时候说道,“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更远,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富有新意的作品来,就要看他‘超越’故乡的能力。”所以顾彬也说,“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
孙甘露 语方实验的极端
“先锋号”上还刊登了孙甘露的实验文体《信使之函》,写这部小说时,他还在邮局工作。“当时,能看到的杂志不多,但却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一个《信使》中文版,我每期都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来看。我在邮局工作,对‘信’当然有敏感性,之后却成了小说的一个灵感所在,通过‘信’观察这个世界。”孙甘露对早报记者说。在先锋作家里,孙甘露在语言的实验上走得最极端,他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尤其是小说语言的诗化。华美,纯净,意想不到的搭配。
孙甘露还回忆,1986年上海作协在茹志鹃主持下开了青年作家创作讲习班,他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程永新,“程永新后来主动向我约稿。当时文坛的情况是,年轻作家不满传统的文学叙事,大家零星地也写了一些所谓与众不同的小说,但《收获》对此很敏感,然后有意识地组织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专号’上推出。我们这批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读者对‘小说’形态的看法,在当时对文坛的震动非常大。”孙甘露对早报记者说。
苏童 早期先锋文本
苏童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青石与河流》,刊登在1986年的第五期上,“在这个杂志上发作品是很难的事情,当时文学小兄弟、小姐妹们都特别羡慕我。”苏童对早报记者说,“《青石与河流》是得到了好朋友黄小初的推荐,他把小说推荐给了程永新,第二年,程永新就向我约稿了,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程永新约到的稿就是后来发表在“专号”上的《1934年的逃亡》,虽然这部小说上了著名的“先锋号”,但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他却说,这部小说只是“仿寻根”小说,“《青石与河流》和《1934年的逃亡》都是我当时对社会思潮——特别是寻根思潮的回应,我把这两部小说看作是自己‘仿寻根’小说。《青石与河流》里面没有我个人的经验,都是我个人阅读的想象,而《1934年的逃亡》里面的家庭史有一点我母亲那边家族的影子。但是,这两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之后,我马上自觉意识到,要摆脱这样一种模仿的写作状态,急于希望脱身,寻找自己的写作状态。”然后就有了1987年底发表在《收获》上的《罂粟之家》,它虽然还是家庭史的写作,但小说的文体和视角都是非常独特的,“摆脱了寻根文学对我的束缚”,后来评论界也把它当作“先锋文学的早期文本”。
格非 草坪上的迷宫
“先锋作家”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非则很遗憾地错过了“先锋号”,在1987年第六期上,他推出了代表作《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顷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格非的小说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但跟马原不同,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线圈式的迷宫,不同的人的理解和诠释会截然不同。
谈起这部成名之作,格非对早报记者说,“1986年的时候《追忆乌攸先生》发表了,我觉得可以写点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决定写第二篇小说,也就是《迷舟》。当时每天晚上大概四五点钟,我和女友在华师大文史楼前面的大草坪见面。每天我们在固定的地点——一棵树边上,拿报纸垫着,坐在那里聊要写什么,然后我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要写一个警卫员,一定要把他隐藏得很深,任何人都察觉不到这个人会杀死他的旅长。”“我有了这个想法后就很兴奋,于是我们就商量怎么写。我就是要写命运的偶然性、不可捉摸,我当时对这个题材已经很着迷了,在我看来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可能去把握的。当时我对中国历史也作了一些研究,感想特别的多,于是就想写这个来暗示历史、暗示命运。当时我给她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她也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很好。然后我们就讨论要把这个故事放到哪个年代。我不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形象,需要的是一个中立的人物,于是我就想到北伐,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点儿北伐方面的书。《迷舟》很快就写完了。写《迷舟》的时候,我同样感觉特别好,特别激动,好像在你眼前铺展开来的一切都是新的。”
写完《迷舟》以后,格非就拿给好朋友吴洪森看,当时他和《上海文学》的关系特别好,他带着稿子去找周介人——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上海文学》就把稿子退回来了,“周介人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说实话,我当时很激动,觉得主编居然给我写退稿信,而且写得很长,指出我小说的不足,说我的这篇小说是通俗小说,所以不能在《上海文学》发表。吴洪森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让我把小说给《收获》,当时我想《上海文学》都不发,《收获》怎么可能发呢?第二天,李洱陪着我又跑到作家协会去了。”
“《收获》的编辑程永新让我把稿子放下,我们就走了。回到学校我想,肯定没戏。过了几个月,我实在等不及了,想这个小说要是不发那我就拿回来好了。于是我就给程永新打电话,冷冷地说,‘请你们把稿子给我寄回来吧。’他说:‘寄什么寄?早就给你发了。’”格非说,手稿上贴了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图,当时《收获》居然觉得这图很重要,把图也印上去了。
苏童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那时候我是中学生,就想考个好大学。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金融风暴早点过去。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红楼梦》。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人变老了,心变年轻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做错的事情纠正,好的事情做得更好。
现在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你喜欢快还是慢?
我一直喜欢慢的生活节奏。
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没有。南京就是我理想的居住城市。
韩东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一时真记不起了。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不要害人。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太多了,真想不起来。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变老了,这是最大的变化。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还是去写东西。
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人实在太多了,想清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