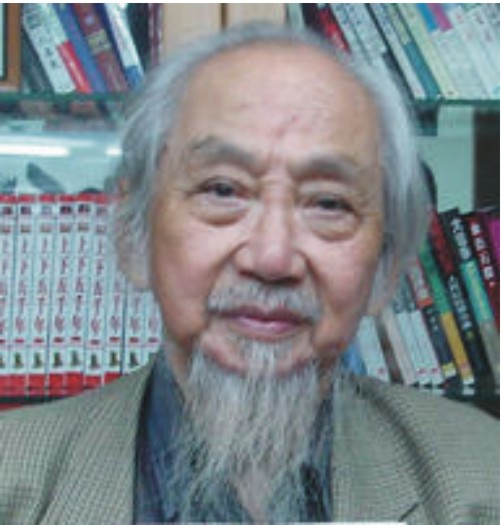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张爱玲遗札 十四年后终于送达
作者: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09-3-10 点击次数:
| 张爱玲生前拟付邮寄往上海的一封感谢信和赠送收信人的一只女式小钱包,在相隔漫长的整整14年之后,终于安妥地送达收信人之手。这不啻是一个张爱玲式的“传奇”,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真实,那么温馨,不仅深深感动了收信人,也提醒我们对张爱玲晚年生活和心境有全面认识的必要。 1 事情的经过需回溯到去年12月20日。我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一位陌生的刘晓云女士向我详细通报内地不断发生的虐猫事件(因为我是“爱猫族”,编选过《猫啊,猫》一书),建议我给予必要的关注。通话结束前,她顺便提到了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张爱玲把她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委托台北皇冠出版社编辑方丽婉女士寄赠我时,也寄赠了她一册。换言之,当时内地收到张爱玲赠书的并非我一人,而是她与我。 我的已经有点模糊的记忆一下子被激活了。她的话使我想起了当年与张爱玲姑夫李开弟先生(1902—1997)在一起时,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过他的这位爱读张爱玲的“小朋友”。查我1995年9月9日在张爱玲逝世后所作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附记”,我收到张爱玲赠书是在1995年春节前夕,是大年初一的1月31日。由此可以推断,张爱玲传真方丽婉女士嘱寄赠书给我,当在1995年1月初前后,刘女士收到赠书应该也在同一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下面还会提到。 如果说刘女士这次与我联系纯属平常,那么接下来的戏剧性进展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今年1月14日下午,我乘到香港参加会议之便,由马家辉先生引介,专诚拜访宋淇先生公子宋以朗先生,有幸浏览了他保存和整理的丰富而又珍贵的张爱玲资料,包括各种中英文手稿、信札、剪报和相关证件等等。最后,以朗先生又向我们出示三小包东西,说这三件张爱玲遗物他不知该如何处理。 这是三个相同的长方形厚牛皮纸信封,里面各有一通张爱玲亲笔信和一只小钱包。第一封信致“KD”,即已经去世的张爱玲姑父李开弟先生;第二封信致“斌”,其人待考;第三封信致“晓云小姐”。当我阅毕第三封信,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晓云小姐”不就是刘晓云女士吗? 张爱玲致“晓云小姐”的这封信写在一款“MADE IN U.S.A”的对折花卉贺卡上,贺卡大小尺寸为12.2×18.4cm,封面为粉红底色上印着一朵含苞怒放的白百合花。张爱玲在打开后的右边题词页上用黑色水笔竖写着: 晓云小姐, 为了我出书的事让您帮了我姑父许多忙,真感谢。近年来苦于精力不济,赠书给友人都是托出版社代寄,没写上下款,连这点谢忱都没表达,更觉耿耿于心。这小钱包希望能用。祝 前途似锦 张爱玲 信中所说的“小钱包”为奶青色,白鳝皮质地,大小尺寸为10.6×7.4cm,也是对折,打开之后,左为证件夹,右为大小两格的钱夹,大钱夹内里缝有印着“MADE IN KOREA ”字样的黑绸标签。这贺卡,这女式小钱包,大概都是张爱玲在她最后四年居住的洛杉矶Rochester Ave.公寓附近超市选购的吧?从中或可看出张爱玲挑选这类小物件的品位。 2 有必要对张爱玲这封写给“晓云小姐”的信略作考释,以确定“晓云小姐”就是刘晓云女士。这个工作并不困难,此信首句就证实了“晓云小姐”与刘女士确为同一人。李开弟先生是中国九三学社社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刘女士在九三学社任职,随九三学社有关负责人拜访老社员时结识了李先生,当时张爱玲姑姑张茂渊女士也健在。刘女士后来就常去探望,陪两位老人聊天。她原先担任编辑工作,经作家王安忆推荐,已经读过张爱玲的《传奇》,印象深刻,但她开始并不知道这对和蔼可亲的老夫妇与张爱玲的密切关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李开弟先生担任张爱玲著作在内地的版权代理人,《张爱玲散文全编》(1992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和《张爱玲文集》(四卷本,1992年7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初版)等都是李先生授权出版的。在此过程中,刘女士协助李先生做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包括陪同李先生去请教资深法律专家等等。这就是张爱玲信中所说的“为了我出书的事让你帮了我姑父许多忙”的由来。 记得约1994年11、12月间,我拜访李先生,李先生主动说:我正要给张爱玲写信,你研究张爱玲,对张爱玲有什么问题和要求,我可以转达。我就斗胆提出希望得到她的新著签名本留念,因我得知她的《对照记》半年前刚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张爱玲对我不断发掘她早期佚作开始是有看法的,是不以为然的,为此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委婉地表示过我的不同意见。我也注意到张爱玲的态度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一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这次以朗先生提供给我的《爱憎表》首页,张爱玲第一句就说:“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啼笑皆非。”“热心人”的提法终于证实了我的推测。而在当时,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不情之请,其实是受到了李先生的鼓励。一定是李先生在致张爱玲信中除了转达我的请求,也代刘女士向张爱玲索书,并向张爱玲介绍了刘女士,所以张爱玲才会在此信中除了向刘女士表示感谢,同时解释了她为什么无法赠送《对照记》签名本的原因。 3 张爱玲此信未署写信日期,从刘女士1995年1月间收到《对照记》赠书(与我同时收到)的时间推算,此信写于1995年1、2月间的可能性极大。当时张爱玲除了与皇冠出版社、与李开弟先生和极少数几位友人有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外,几乎已与外界隔绝。张爱玲致庄信正先生最后一封信写于1994年10月5日(据庄信正著《张爱玲来信笺注》,2008年3月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初版),致夏志清先生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5月5日(据夏志清作《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载1996年3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致已故林式同先生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5月17日(据林式同作《有缘得识张爱玲》,出处同上)。因此我敢断定,张爱玲致刘女士这封信和同时所写的致李开弟先生和致“斌”的信是她生前最后的“书信演出”之一,是她生前与上海亲友最后的书信因缘。 事实上分别装有这三封信和小钱包的厚牛皮纸信封当时均已用订书钉封口,但信封上均未开列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当然也未能付邮。这原因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张爱玲在世的最后几年体弱多病,她“苦于精力不济”,平时已很少外出,此时更少外出,或者她被别的什么事耽搁了,以至她直到六七个月后谢世也未能如愿寄出这三封信和礼物。 4 世事难料,仿佛冥冥之中上苍自有安排。如果刘女士去年12月20日不给我来电,如果我1月10日不去拜访以朗先生,如果以朗先生不出示张爱玲未能付邮的这三封信,那么,致“晓云小姐”这封信收信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也就不会浮出历史地表,这个感伤动人的故事也就不会有如此圆满的结局了。 受以朗先生委托,我携此信和女式小钱包返沪,在春节过后的2月10日,把它们连同留有张爱玲手泽的厚牛皮纸信封一起妥善交到刘晓云女士手中。她万万没想到张爱玲在14年前给她写过信,而她在整整14年之后竟然还能收到这封信!刘女士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她感谢张爱玲,也感谢李开弟先生,在次日给我的信中表示:“收到爱玲女士遗赠墨宝,内心震动,感慨万千,无以言表,眼眶一直潮湿。以爱玲女士之高贵、之才华、之隆誉谁人能比肩?然她对一素不相识普通人之用心又谁能如此?” 正如刘女士所说,对张爱玲而言,这封信是写给一位“素不相识普通人”的,这在张爱玲一生中恐怕是很少见的,在她后期生涯中更是绝无仅有的。但从信中流露的亲和,从她挑选的小礼物,自可真切地感受到张爱玲温柔敦厚、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感受到张爱玲出自内心的谢忱和祝愿。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张爱玲70年代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所任职时,收到同事关心她身体而为她配制的草药后,以CHANEL NO.5香水回赠这件事(详见陈少聪作《与张爱玲擦肩而过》,载2006年3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记忆张爱玲》),也许这样的联想有点不伦不类。不管怎样,刘晓云女士是幸运的,她终于收到了张爱玲这封弥足珍贵的遗札!有论者认为张爱玲的后期书信“无法让人不将之视为她的另一种创作”(引自苏伟贞作《信还魂》),我深以为然。也因此,我看重张爱玲此信的意义。 我为能在张爱玲写下此信14年之后参与送达,终于完成张爱玲未了的遗愿而感到高兴。 |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