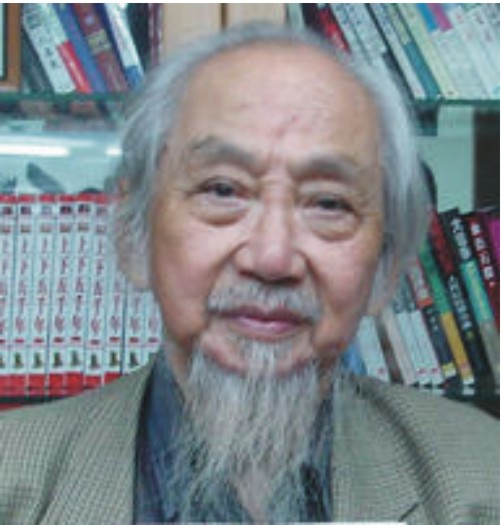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李浩:愿把小说变成“智慧之书”
作者: 来源:文学报 金莹 发布时间:2009-3-29 点击次数: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海兴县辛集村。当过八年的小社员。”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作家李浩自书的简介上的第一句。这样简单而低调的开始,似乎也预示着他在生活与写作中的态度。
和给人“忠厚而粗犷,言谈木讷,表情羞涩”的印象恰相反的是,“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评论家崔庆蕾和吴义勤这样评价李浩的写作。
“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请谈谈你最初的文学启蒙,以及你的创作历程。
李浩:我的文学爱好大约产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中学教书的父亲订阅了一些诸如《中篇小说选刊》《儿童文学》之类的杂志,家里也有一些小说,它们成为我最初的滋养。
在初中那个爱做梦的年龄,我突然爱上了诗歌,当时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李煜对我产生了致命而有益的影响。我和他骨子里有特别的契合,也有那种对时间、生命的吁叹;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真实表达”,学到了“欲语还休”;他给我的性格建立了某种基调。或者说,我有这种基调,被他唤醒了。我对后现代某些理念的认同和李煜给我的这种唤醒有很大关系。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但在我的印象中,你的写作似乎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多?
李浩:我在中学时的成绩不好,后来到沧州师范学校上学,学美术专业。在那里,我开始接触朦胧诗和西方现代文学。要知道,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叫我“满清遗少”,学古诗,写繁体字,画国画……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一些人。不然,我可能会固执傲慢地宣称朦胧诗以降的诗和西方现代文学不是文学,我原来学的那些才是……
我怀念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文学社和艺术社。在那个时候,大家有种特别的对知识的渴望。谈一本书,如果你没有读到,会有强烈的羞耻感。我爱这份虚荣,我也准备保持这份虚荣一生。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博尔赫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有许多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参与了我血脉的塑造。
记者:你还说过你比较欣赏胡适等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什么特质最打动你?
李浩:不只是胡适,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他们所给我的启示是:一,不狭私,在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对他人和另外的学说抱有理解和体谅,不以为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同时,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甚至可不断地否定自己。二,对知识的敬重,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中,而且总是感觉自己无知。三,对世界的关爱,对他人的关爱。当下的知识分子中优秀者也不少,只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时间会让这些人的价值慢慢显现的。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缺少幽默感,媚俗,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文学的三大敌人。”这不只是文学的敌人,也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敌人。我觉得,文学的作用或者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应当是:将我们从一种对美的麻木感中解脱出来,从一种习惯性的错谬中解脱出来,从对流行思想的盲目遵从中解脱出来。它有抵抗下滑的作用。而当下的状态恰是,文学和文化在某方面加速着这种下滑。我想,一个民族,多数人迷恋浅俗的快乐不可怕,但知识分子再推波助澜则有些可怕;一个民族,多数人渴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但知识分子,也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则有些可怕。作家应当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而不应是在其外。文学,文化,有一部分应当变成智慧之书,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山峰……
“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
记者:你所写的故事没有归于一定的题材,但都可令人感觉到在文字之外,试图表达着一些精神性的思考。
李浩:我的写作很大程度是“概念先行”“思想先行”,也就是说,每写一篇作品,我都要想,我的这篇小说(或诗歌)有无独特的发现和提供?它是不是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同时,我也要问,它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上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我有无媚俗媚众的倾向?在此之后,我觉得我要写的小说要有个人的思考在,在当下的写作中有一定的异质性,同时它又是艺术的,有着结构和语调上的美感,才开始写。当然,部分小说是出于怕自己长时间不写手生而勉力写出,这样的写作少之又少,而且多数不发表。
在我看来,小说应当是对人的追踪和塑造,是对人性隐秘的探寻与挖掘。我认为,写人和写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下的小说,写事的多,写人的很少,当然,事写好了也是非常伟大的,我只是表明我个人的趣味和倾向。我想,“我思,故我在”能很好地说明我的写作:如果取消小说中的思考和智慧成分,我的小说的存在也就可以取消了。我愿意,把我的小说变成一种“智慧之书”。
我说的智慧,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哲学、社会学中的“科学理性”。在我小说中的思,可以是歧义,可以是模糊,可以是一种严肃的滑稽戏……但它们,都不是轻质的,都指向我们的生存。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想表达的东西?李浩:最早,我的小说所致力的是“为小人物立传”,像《生存中的死亡》《英雄的挽歌》等。我想写我的亲人、我所熟悉的农民身上的卑微、自私、温良和隐秘的恶,世故与不抱希望……有一段时间,我在反思我和我们的理想,于是写下《如归旅店的叙事》《失败之书》等。另一个阶段,我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特别的兴趣,当然,更关注的是他们在知识理念和生活理念中的两难与挣扎,所以我写下了《告密者札记》《夏冈的发明》……我承认,我在思考中,也时时面临着两难和挣扎,面临对自己和自己理想的质疑,在我的身上,也流着和他们相同的血。我还写过其它类型的小说,我得说,它们无一不指向生存之内,无一不指向智慧和思考的可能。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个词,叫“侧面的镜子”,它说出的是对我写作的理解:小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放在我身体侧面的镜子,我要借用它来说出我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说出我的爱与悲、欢愉和痛苦,说出我的怯懦与困惑,同时,我承认,它对我也是一种精神补偿:我要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来完成我今生所不可能完成的某些事。
我不会停止自己的冒险,尽管我知道退一步有可能海阔天空。但,这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我只有在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干这个的料的时候再这样做吧。现在,我还不死心。
记者:从你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技巧的注重。
李浩:我从来都不轻视技术,这大约和我学习绘画的经历有关,我多少都可算那种技术主义者。
我很不认同那种经历了怎么写现在应当考虑写什么的说法,中国画中有一个说法,叫“随类赋形”,就是说,你的表达手法和方式是随你表达的内容之变化而变化的,除非你不再冒险和前行,只是重复。我不信任任何一种能将所谓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的解剖学。没有技术,肯定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小说。取消了这种精心,小说的味也就取消了,妙也丧失了。我们当下的小说,确有忽略小说技术和语言特色的危险。
“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
记者:你如何看待如今越来越面对无力抵挡市场大潮的文学?
李浩:我很欣赏一句话,叫“写给无限的少数”,它要求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写给少数的,但必须保证它具有可能“无限”的品质,跨越他所生存时代的品质。这更是我所看中的。
对于文学从高堂到边缘这一点上,我愿意和许多的同行保持一致,承认它有进步的一面。但也有一点,是应当让这个时代和社会警醒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和欲望是不是太单一化了,我们的生活追求中是不是从一种缺少到了另一种缺少?全民性的不读书,不尊重知识和智慧,肯定是个问题。“娱乐至死”“读图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统一病症,这个病症也不只是在我们中国。美国文化是始作俑者。至于当下文学,出现这种状况也有它的自身问题:你能给人提供的有多少?
当前,平庸而“过于顺畅”的叙事,叙事多样性的丧失,“事件”背后的苍白以及集体性的不思考不冒险,使当下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无新意无趣味的“空转”状态,我们的确无力面对种种指控。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受着无序市场诉求的挤压和某些陈规旧习、滞后观念的挤压。媚俗化倾向损害到了文学,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损害到了文学,常识未明损害到了文学(对纯文学的误解即是一例),尤其严重的是,敬畏和爱的消褪也损害到了文学。某些文学从业者的自我轻贱也让人厌恶。
当下,我们强调市场强调得太多了。普及工作必须有人做,但如果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做普及,变成大众明星,也是一件可笑的事。
记者:你写小说、诗歌,评论等等,但似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李浩:在我的写作中,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一般而言,我在情绪特别充沛或者是被激情冲撞着的时候写诗,而小说,是一个绵长之物,它是一天天在想,一天天在写。我愿意在我的小说中放置诗歌。我没有写过长篇,是因为力有未逮,这是事实。一旦有了能力我还是要写的。
我的野心当然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有思考纵深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让后世的人、国外的人反复阅读的作家。我不知道我的能力能不能支撑我的野心。有时对此很焦虑,对自己很怀疑,甚至是绝望。但我也有自己的阿Q胜利法。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写。
和给人“忠厚而粗犷,言谈木讷,表情羞涩”的印象恰相反的是,“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评论家崔庆蕾和吴义勤这样评价李浩的写作。
“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请谈谈你最初的文学启蒙,以及你的创作历程。
李浩:我的文学爱好大约产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中学教书的父亲订阅了一些诸如《中篇小说选刊》《儿童文学》之类的杂志,家里也有一些小说,它们成为我最初的滋养。
在初中那个爱做梦的年龄,我突然爱上了诗歌,当时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李煜对我产生了致命而有益的影响。我和他骨子里有特别的契合,也有那种对时间、生命的吁叹;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真实表达”,学到了“欲语还休”;他给我的性格建立了某种基调。或者说,我有这种基调,被他唤醒了。我对后现代某些理念的认同和李煜给我的这种唤醒有很大关系。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但在我的印象中,你的写作似乎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多?
李浩:我在中学时的成绩不好,后来到沧州师范学校上学,学美术专业。在那里,我开始接触朦胧诗和西方现代文学。要知道,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叫我“满清遗少”,学古诗,写繁体字,画国画……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一些人。不然,我可能会固执傲慢地宣称朦胧诗以降的诗和西方现代文学不是文学,我原来学的那些才是……
我怀念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文学社和艺术社。在那个时候,大家有种特别的对知识的渴望。谈一本书,如果你没有读到,会有强烈的羞耻感。我爱这份虚荣,我也准备保持这份虚荣一生。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博尔赫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有许多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参与了我血脉的塑造。
记者:你还说过你比较欣赏胡适等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什么特质最打动你?
李浩:不只是胡适,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他们所给我的启示是:一,不狭私,在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对他人和另外的学说抱有理解和体谅,不以为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同时,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甚至可不断地否定自己。二,对知识的敬重,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中,而且总是感觉自己无知。三,对世界的关爱,对他人的关爱。当下的知识分子中优秀者也不少,只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时间会让这些人的价值慢慢显现的。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缺少幽默感,媚俗,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文学的三大敌人。”这不只是文学的敌人,也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敌人。我觉得,文学的作用或者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应当是:将我们从一种对美的麻木感中解脱出来,从一种习惯性的错谬中解脱出来,从对流行思想的盲目遵从中解脱出来。它有抵抗下滑的作用。而当下的状态恰是,文学和文化在某方面加速着这种下滑。我想,一个民族,多数人迷恋浅俗的快乐不可怕,但知识分子再推波助澜则有些可怕;一个民族,多数人渴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但知识分子,也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则有些可怕。作家应当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而不应是在其外。文学,文化,有一部分应当变成智慧之书,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山峰……
“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
记者:你所写的故事没有归于一定的题材,但都可令人感觉到在文字之外,试图表达着一些精神性的思考。
李浩:我的写作很大程度是“概念先行”“思想先行”,也就是说,每写一篇作品,我都要想,我的这篇小说(或诗歌)有无独特的发现和提供?它是不是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同时,我也要问,它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上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我有无媚俗媚众的倾向?在此之后,我觉得我要写的小说要有个人的思考在,在当下的写作中有一定的异质性,同时它又是艺术的,有着结构和语调上的美感,才开始写。当然,部分小说是出于怕自己长时间不写手生而勉力写出,这样的写作少之又少,而且多数不发表。
在我看来,小说应当是对人的追踪和塑造,是对人性隐秘的探寻与挖掘。我认为,写人和写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下的小说,写事的多,写人的很少,当然,事写好了也是非常伟大的,我只是表明我个人的趣味和倾向。我想,“我思,故我在”能很好地说明我的写作:如果取消小说中的思考和智慧成分,我的小说的存在也就可以取消了。我愿意,把我的小说变成一种“智慧之书”。
我说的智慧,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哲学、社会学中的“科学理性”。在我小说中的思,可以是歧义,可以是模糊,可以是一种严肃的滑稽戏……但它们,都不是轻质的,都指向我们的生存。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想表达的东西?李浩:最早,我的小说所致力的是“为小人物立传”,像《生存中的死亡》《英雄的挽歌》等。我想写我的亲人、我所熟悉的农民身上的卑微、自私、温良和隐秘的恶,世故与不抱希望……有一段时间,我在反思我和我们的理想,于是写下《如归旅店的叙事》《失败之书》等。另一个阶段,我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特别的兴趣,当然,更关注的是他们在知识理念和生活理念中的两难与挣扎,所以我写下了《告密者札记》《夏冈的发明》……我承认,我在思考中,也时时面临着两难和挣扎,面临对自己和自己理想的质疑,在我的身上,也流着和他们相同的血。我还写过其它类型的小说,我得说,它们无一不指向生存之内,无一不指向智慧和思考的可能。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个词,叫“侧面的镜子”,它说出的是对我写作的理解:小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放在我身体侧面的镜子,我要借用它来说出我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说出我的爱与悲、欢愉和痛苦,说出我的怯懦与困惑,同时,我承认,它对我也是一种精神补偿:我要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来完成我今生所不可能完成的某些事。
我不会停止自己的冒险,尽管我知道退一步有可能海阔天空。但,这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我只有在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干这个的料的时候再这样做吧。现在,我还不死心。
记者:从你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技巧的注重。
李浩:我从来都不轻视技术,这大约和我学习绘画的经历有关,我多少都可算那种技术主义者。
我很不认同那种经历了怎么写现在应当考虑写什么的说法,中国画中有一个说法,叫“随类赋形”,就是说,你的表达手法和方式是随你表达的内容之变化而变化的,除非你不再冒险和前行,只是重复。我不信任任何一种能将所谓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的解剖学。没有技术,肯定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小说。取消了这种精心,小说的味也就取消了,妙也丧失了。我们当下的小说,确有忽略小说技术和语言特色的危险。
“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
记者:你如何看待如今越来越面对无力抵挡市场大潮的文学?
李浩:我很欣赏一句话,叫“写给无限的少数”,它要求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写给少数的,但必须保证它具有可能“无限”的品质,跨越他所生存时代的品质。这更是我所看中的。
对于文学从高堂到边缘这一点上,我愿意和许多的同行保持一致,承认它有进步的一面。但也有一点,是应当让这个时代和社会警醒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和欲望是不是太单一化了,我们的生活追求中是不是从一种缺少到了另一种缺少?全民性的不读书,不尊重知识和智慧,肯定是个问题。“娱乐至死”“读图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统一病症,这个病症也不只是在我们中国。美国文化是始作俑者。至于当下文学,出现这种状况也有它的自身问题:你能给人提供的有多少?
当前,平庸而“过于顺畅”的叙事,叙事多样性的丧失,“事件”背后的苍白以及集体性的不思考不冒险,使当下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无新意无趣味的“空转”状态,我们的确无力面对种种指控。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受着无序市场诉求的挤压和某些陈规旧习、滞后观念的挤压。媚俗化倾向损害到了文学,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损害到了文学,常识未明损害到了文学(对纯文学的误解即是一例),尤其严重的是,敬畏和爱的消褪也损害到了文学。某些文学从业者的自我轻贱也让人厌恶。
当下,我们强调市场强调得太多了。普及工作必须有人做,但如果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做普及,变成大众明星,也是一件可笑的事。
记者:你写小说、诗歌,评论等等,但似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李浩:在我的写作中,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一般而言,我在情绪特别充沛或者是被激情冲撞着的时候写诗,而小说,是一个绵长之物,它是一天天在想,一天天在写。我愿意在我的小说中放置诗歌。我没有写过长篇,是因为力有未逮,这是事实。一旦有了能力我还是要写的。
我的野心当然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有思考纵深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让后世的人、国外的人反复阅读的作家。我不知道我的能力能不能支撑我的野心。有时对此很焦虑,对自己很怀疑,甚至是绝望。但我也有自己的阿Q胜利法。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写。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