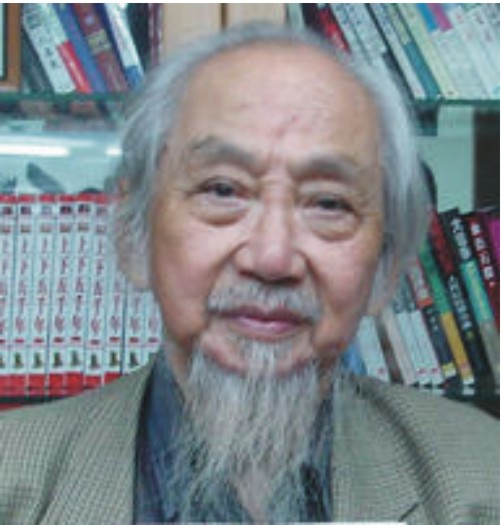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苏童 让它在纸上等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石剑峰 发布时间:2009-4-10 点击次数:
在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时隔三年,作家苏童的最新长篇小说《河岸》在最新一期《收获》杂志发表,20万字的小说单行本也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与三年前的“重述神话”不同的是,《河岸》重拾苏童熟悉的江南城镇题材,小说时间背景也是苏童那辈作家喜欢的“文革”。小说讲述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展现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书写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境遇。争夺军烈属身份、检验屁股上的胎记、剪断阴茎……这些荒诞的元素依然是苏童或者余华他们热衷的符号。
在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苏童身在加拿大,一如小说的初稿在德国莱比锡写成。苏童在德国莱比锡与世隔绝地居住三个月,在“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中写下了《河岸》初稿,但后来都没用在小说中,“没有人打扰过我,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苏童说。《河岸》的创作历经两年,苏童说写这样一个小说完全是出自个人愿望,“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
相对比其他作家,苏童的长篇小说产量非常低,他的主业还是中短篇,作家王安忆称赞苏童是中国最会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不过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苏童也毫不避讳谈论长篇小说创作的艰苦,但他又说,“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而短篇小说“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在采访中,苏童对自己这部新长篇充满期待。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已有近一个月,而在读者和评论家中的回响非常微弱。对此,苏童只是说:“让小说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
早报:三年前的重述神话《碧奴》其实是个命题作文,那这次写《河岸》呢?这部长篇小说重归你擅长的历史叙事加典型江南城镇。
苏童:小说的创作前后大约两年时间,是一个愿望促成了这部小说。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小说最初的创作在莱比锡,写了一半篇幅,后来几乎没用上。我在那城市独自居住了三个月,非常喜欢那儿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早报:小说名叫《河岸》,在小说中,“河”、“岸”和“船”各自象征了什么呢?
苏童:这部小说如果要用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应该是叫“河与岸”,但是我想还是叫“河岸”更加自然一些。在小说中,我无意用河与岸或者船去象征什么,但我确实试图通过这三足鼎立的事物建立一个维度,去观察人的处境,船与河是一组关键词,房屋与岸是另一组关键词,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与其说是象征,不如说我是在探索这组参照物的奥秘,因此,并不是那么悲伤,背后有一种乐观主义在支撑。
早报:长篇小说《河岸》让我想起你另外一篇小说《西瓜船》,两部小说都有“船”、“河流”和“寻找”的意象。在你看来,这两部小说诉求不同之处在哪里?
苏童:《河岸》与《西瓜船》的叙述诉求是不一样的。《西瓜船》中,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读者记住那个乡下母亲独自从城里摇船回家的情景,那船上有她儿子的血迹。《河岸》复杂许多,我其实说了三个半孤儿的故事,库文轩、慧仙和傻子扁金都是孤儿,主人公库东亮是半个孤儿,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母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家园的故事,或者干脆说,是他们寻找幸福的故事。
这几个人物都被命运放逐或者遗弃,走到一起去了,他们与河水有纠葛,与岸有纠葛,他们之间也有密集的纠葛,他们注定有天生的不幸,而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动作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该寻找什么呢,我想他们首先要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
早报:不过库家父子的寻找之旅不太惊险。
苏童:库家父子找得很辛苦,当然不惊险,但是很疲惫,因为过于疲惫,库文轩去了河底,也因为过于疲惫,库东亮决定留在河上。
早报:在这部小说里,你使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话语,还用粗体字加重,但并没有觉得突兀,你刻意这样书写是为了什么?
苏童:我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所尽知的荒诞年代,荒诞是不用去揭露的,人在荒诞年代中的沉重处境才需要被关注,所以,叙事策略需要设置轻与重的关系,荒诞年代是轻的,荒诞年代中的人生则是重的。
早报:小说的背景是“文革”,但你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似乎非常节制,历史或意识形态并非小说的重点,是否这样?
苏童:《河岸》里有明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我的故事背景。与我以前写作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我试图用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勾勒这个时代的面孔,因此,《河岸》里的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对于这个最大的人物,我更多的不是利用所谓的记忆,而是用理性去勾画他的面孔,因此这个人物其实是最嚣张、最狂暴的。
早报:也正因为如此你在小说中对暴力的使用还是非常节制的。
苏童:有的地方读起来还是有暴力的嫌疑,比如由半个孤儿库东亮施予另一个孤儿傻子扁金的暴力,尽管我努力回避,但终究回避不了,我听从生活逻辑的支配。这个故事里,暴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施暴与被施暴是人物的处境之一。
早报:尽管小说是个悲剧,但在阅读中还是对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小情绪描写非常期待,这本来是你的长项,但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呢?
苏童:在库东亮身上,我写的其实是他的性压抑,他对慧仙的情感处于健康与不健康的夹缝中,他是单相思,慧仙对库东亮的爱没有呼应,也不该呼应。库东亮不仅被他父亲禁锢,其实他自己也禁锢了自己。我如果去写这对少男少女的恋爱,那完全是自己想和他们谈恋爱了。
“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
早报:王安忆说,她对你的虚构能力十分佩服,这部小说是否也是完全虚构的产物?船队的故事,原本可以写得很荒诞,你却克制,为什么?
苏童:几乎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我从小临河而居,见过无数的内河船队来来往往,但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有点特别,这是一支“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去了,这些放逐者被惩罚了,同时也被解救了,他们是收留库家父子的诺亚方舟。这并不荒诞离奇。这是我重笔渲染的一个局促的天堂。
早报:大家认为,你最擅长、最能给读者带来欣喜的是中短篇小说创作。创作这部小说,最大的困难在哪?
苏童:从体力感觉上说,长篇与短篇的区别,大概就是跑马拉松和百米的区别。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很艰辛,但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你一个人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打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的生活,很疲惫,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膝下儿女无数,辛苦一场,但最后他们全部离开了你,成为读者的记忆,你还要操心他们谁是读者记忆中的好孩子,谁是坏孩子,更要焦虑,你将被证明是什么样的父母。短篇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很像一支歌,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早报:《河岸》中虽然有些荒诞的因素,但和你早期创作相比,包括这部长篇小说在内,你近几年的作品都不走边锋不求怪,都在朴素生活里的材料里写故事,这对你的创作是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答:求怪得怪,剑走偏锋,都以文本的成败论英雄,无所谓好与坏。朴素倒永远是一个褒义词,细细考量,写得朴素,其实是一个极高极高的境界,说自己朴素其实是夸自己呢!所有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都相仿,其实就是寻求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哪条路是康庄大道,但大家都相信康庄大道一定是从尘土中走出来的,说到底,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早报:你对这部新长篇还是充满期待,但我从一些评论家和读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暂时无法对《河岸》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无法说好在哪里,但也并不觉得坏,你怎么看大家对你作品的这样一种反应?
答: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的反应,我对这事的反应几乎异曲同工,无法说高兴,但也并不觉得不高兴。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
与三年前的“重述神话”不同的是,《河岸》重拾苏童熟悉的江南城镇题材,小说时间背景也是苏童那辈作家喜欢的“文革”。小说讲述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展现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书写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境遇。争夺军烈属身份、检验屁股上的胎记、剪断阴茎……这些荒诞的元素依然是苏童或者余华他们热衷的符号。
在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苏童身在加拿大,一如小说的初稿在德国莱比锡写成。苏童在德国莱比锡与世隔绝地居住三个月,在“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中写下了《河岸》初稿,但后来都没用在小说中,“没有人打扰过我,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苏童说。《河岸》的创作历经两年,苏童说写这样一个小说完全是出自个人愿望,“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
相对比其他作家,苏童的长篇小说产量非常低,他的主业还是中短篇,作家王安忆称赞苏童是中国最会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不过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苏童也毫不避讳谈论长篇小说创作的艰苦,但他又说,“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而短篇小说“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在采访中,苏童对自己这部新长篇充满期待。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已有近一个月,而在读者和评论家中的回响非常微弱。对此,苏童只是说:“让小说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
早报:三年前的重述神话《碧奴》其实是个命题作文,那这次写《河岸》呢?这部长篇小说重归你擅长的历史叙事加典型江南城镇。
苏童:小说的创作前后大约两年时间,是一个愿望促成了这部小说。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小说最初的创作在莱比锡,写了一半篇幅,后来几乎没用上。我在那城市独自居住了三个月,非常喜欢那儿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早报:小说名叫《河岸》,在小说中,“河”、“岸”和“船”各自象征了什么呢?
苏童:这部小说如果要用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应该是叫“河与岸”,但是我想还是叫“河岸”更加自然一些。在小说中,我无意用河与岸或者船去象征什么,但我确实试图通过这三足鼎立的事物建立一个维度,去观察人的处境,船与河是一组关键词,房屋与岸是另一组关键词,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与其说是象征,不如说我是在探索这组参照物的奥秘,因此,并不是那么悲伤,背后有一种乐观主义在支撑。
早报:长篇小说《河岸》让我想起你另外一篇小说《西瓜船》,两部小说都有“船”、“河流”和“寻找”的意象。在你看来,这两部小说诉求不同之处在哪里?
苏童:《河岸》与《西瓜船》的叙述诉求是不一样的。《西瓜船》中,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读者记住那个乡下母亲独自从城里摇船回家的情景,那船上有她儿子的血迹。《河岸》复杂许多,我其实说了三个半孤儿的故事,库文轩、慧仙和傻子扁金都是孤儿,主人公库东亮是半个孤儿,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母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家园的故事,或者干脆说,是他们寻找幸福的故事。
这几个人物都被命运放逐或者遗弃,走到一起去了,他们与河水有纠葛,与岸有纠葛,他们之间也有密集的纠葛,他们注定有天生的不幸,而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动作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该寻找什么呢,我想他们首先要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
早报:不过库家父子的寻找之旅不太惊险。
苏童:库家父子找得很辛苦,当然不惊险,但是很疲惫,因为过于疲惫,库文轩去了河底,也因为过于疲惫,库东亮决定留在河上。
早报:在这部小说里,你使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话语,还用粗体字加重,但并没有觉得突兀,你刻意这样书写是为了什么?
苏童:我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所尽知的荒诞年代,荒诞是不用去揭露的,人在荒诞年代中的沉重处境才需要被关注,所以,叙事策略需要设置轻与重的关系,荒诞年代是轻的,荒诞年代中的人生则是重的。
早报:小说的背景是“文革”,但你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似乎非常节制,历史或意识形态并非小说的重点,是否这样?
苏童:《河岸》里有明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我的故事背景。与我以前写作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我试图用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勾勒这个时代的面孔,因此,《河岸》里的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对于这个最大的人物,我更多的不是利用所谓的记忆,而是用理性去勾画他的面孔,因此这个人物其实是最嚣张、最狂暴的。
早报:也正因为如此你在小说中对暴力的使用还是非常节制的。
苏童:有的地方读起来还是有暴力的嫌疑,比如由半个孤儿库东亮施予另一个孤儿傻子扁金的暴力,尽管我努力回避,但终究回避不了,我听从生活逻辑的支配。这个故事里,暴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施暴与被施暴是人物的处境之一。
早报:尽管小说是个悲剧,但在阅读中还是对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小情绪描写非常期待,这本来是你的长项,但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呢?
苏童:在库东亮身上,我写的其实是他的性压抑,他对慧仙的情感处于健康与不健康的夹缝中,他是单相思,慧仙对库东亮的爱没有呼应,也不该呼应。库东亮不仅被他父亲禁锢,其实他自己也禁锢了自己。我如果去写这对少男少女的恋爱,那完全是自己想和他们谈恋爱了。
“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
早报:王安忆说,她对你的虚构能力十分佩服,这部小说是否也是完全虚构的产物?船队的故事,原本可以写得很荒诞,你却克制,为什么?
苏童:几乎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我从小临河而居,见过无数的内河船队来来往往,但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有点特别,这是一支“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去了,这些放逐者被惩罚了,同时也被解救了,他们是收留库家父子的诺亚方舟。这并不荒诞离奇。这是我重笔渲染的一个局促的天堂。
早报:大家认为,你最擅长、最能给读者带来欣喜的是中短篇小说创作。创作这部小说,最大的困难在哪?
苏童:从体力感觉上说,长篇与短篇的区别,大概就是跑马拉松和百米的区别。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很艰辛,但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你一个人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打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的生活,很疲惫,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膝下儿女无数,辛苦一场,但最后他们全部离开了你,成为读者的记忆,你还要操心他们谁是读者记忆中的好孩子,谁是坏孩子,更要焦虑,你将被证明是什么样的父母。短篇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很像一支歌,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早报:《河岸》中虽然有些荒诞的因素,但和你早期创作相比,包括这部长篇小说在内,你近几年的作品都不走边锋不求怪,都在朴素生活里的材料里写故事,这对你的创作是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答:求怪得怪,剑走偏锋,都以文本的成败论英雄,无所谓好与坏。朴素倒永远是一个褒义词,细细考量,写得朴素,其实是一个极高极高的境界,说自己朴素其实是夸自己呢!所有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都相仿,其实就是寻求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哪条路是康庄大道,但大家都相信康庄大道一定是从尘土中走出来的,说到底,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早报:你对这部新长篇还是充满期待,但我从一些评论家和读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暂时无法对《河岸》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无法说好在哪里,但也并不觉得坏,你怎么看大家对你作品的这样一种反应?
答: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的反应,我对这事的反应几乎异曲同工,无法说高兴,但也并不觉得不高兴。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