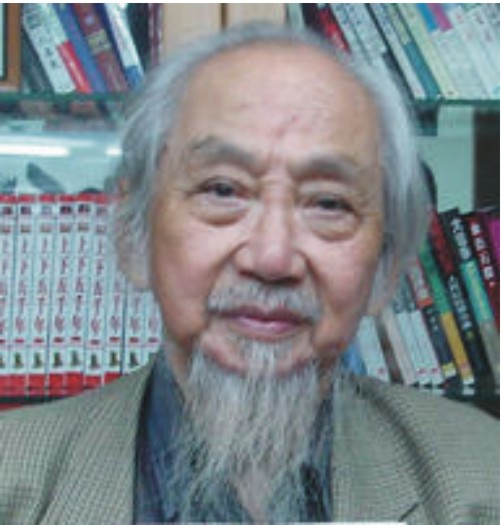哈萨克族民族精神的探索者——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创作
摘 要: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探索者,着力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中表现出的带有本民族特殊印记的流动的文化传统。他的作品既展示了哈萨克人当代生活的风情画面,又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各种各样的时代性的变化。
关键词: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民族精神;探索者
同样是对新疆少数民族人生命运的关注,王蒙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立足点显然不同。王蒙是汉族作家,他对生活在伊犁大地上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是外围透视,俯瞰式的、带着一点微妙的优越感,有着强烈的政治情结的投影。王蒙的创作揭示了人们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政治影响无处不在,社会政治如何成为一个巨大的网,深刻地改变人们生活中的一切,社会政治是左右人们人生命运的决定性的力量,作品中的人物是作为“政治”的人存在的。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探索者,着力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中表现出的带有本民族特殊印记的流动的文化传统,他笔下的人物更具有文化的色彩和性质。他的创作揭示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运动固然改变了或者遮蔽了某些传统风习,但民族文化传统内在的生命力依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哈萨克族,从小读的是汉文学校,可以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语言上的优势,使他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站在一个特殊的高度上,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思考现实生活。所以他的小说题材十分广泛,“有揭露‘四人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小爪牙的,有描写少数民族的人情世故的,也有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一起写的,有写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的,还有一些面向汉族干部的。”[1](P1)而且他的起点比较高,1979年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就获得当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再现了十年“文革”给民族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惨痛伤痕,抒发了主人公心中的压抑和愤懑。虽然作品是跟随“伤痕文学”的潮流,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没有流于“我控诉”式的空洞呐喊。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有着自己观察理解生活的角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而且又有着自己的美学追求。所以他不根据什么观念的套子去填充一点生活经验来敷衍成篇,也不盲目地追逐什么“流派”和“浪潮”。
他的《权衡》、《哈力的故事》、《雄心勃勃》、《发现》、《我的两个学生》、《哈司令、阿尔申别克和他的母亲》、《第二十九任队长》、《履历表上的某一栏》等小说都是以那个特定的年月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在风趣而又犀利地叙述中揭示黑暗势力在种种生活环境中的表现,生动地描摹出那一时代的社会心理历程的发展轨迹,以及生活在这一轨迹中的人们心中难以言传的辛酸与苦涩。在这些作品中,他植根于新疆这块热土,富有色彩地展示了在那个特定年代哈萨克人的质朴而又复杂的灵魂,真正实现了人物性格特色的哈萨克化。
所以艾克拜尔·米吉提笔下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写‘奇装异服’‘奇风异俗’或堆砌听来的与杜撰的‘谚语’,他写的更重神而不在形。”[1](P5)这在他的获奖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中就有精彩的表现:
当他无精打采地磨蹭到自家院门时,巴力斯从拦畜横杆下钻出来,摇头摆尾地迎接主人了。努尔曼收住疲惫的脚步,习惯地端详了一下:巴力斯白得像乳汁,尖鼻子四方嘴,胸脯似虎,腰细如蜂,浑身的短毛被阳光照射得像缎子一样闪闪发光。就连它那褐色的双眸里,也闪耀着通人情的爱娇的光。你看它好像在问:“我的主人,你累了吧?”“不,没有累,没有累,我立刻就能带你去追狐狸呢!”努尔曼摸着巴力斯的头,对它说起话来,“喂,好朋友!等打完草,咱俩得到草原上转转,看碰得上狼不。”猎狗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话,张开大口,鲜红的长舌镰刀般伸出来,哼了两声,在老汉面前一蹦一蹦地撒着欢。老汉觉得方才那阵的乏劲不知忽然间上哪儿去了。这是巴力斯的功劳,方圆多少阿吾勒,就努肯(注:努尔曼自称)才有这样一条好猎狗呢!努尔曼老汉立即振奋起来了。他把芟镰往棚荫下一丢,兴冲冲地喊着:“老婆子,茶炊烧开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说着,轻松愉快地走进屋里。[2](P6)
这一段努尔曼老汉和他的可爱的猎狗巴力斯的描写所表现出的哈萨克族牧人的独特心理特征,是通过人和猎狗之间那种亲昵的感应关系表现出来的。没有对哈萨克族牧人生活切实的感受和体察,是很难将此心理特征表现得如此惟妙惟肖。同样,在《哈力的故事》中,腼腆寡言的牧羊工哈力因为牧羊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牧工,接着“福鸟落顶”一般随“革命形势”的需要成为县委副书记。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专车接送上下班、开会发表“指示性”意见。这个朴实的牧工对权力带来的“特殊化”逐渐都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哈力的黑红脸庞已经变得白皙,肚皮也开始向外鼓出来了。同时还养成了喜欢钓鱼打猎的浪漫习气。如今他走到哪里,马褡裢里总是装着甩钩,在家里还养着一条猎狗,县武装部早为他解决了一支双筒两用猎枪。他还打算今后再设法弄一只阿勒泰山上的白翎鹰养起来……”这些变化明显具有哈萨克族的特点,与哈力的牧工出身相关。这些牧人的爱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哈力身上这些由于借助权力的力量而发生的变化是让人厌恶的,特别是后来他在木沙家用包尔萨克(哈萨克族待客的油果子)喂自己的猎狗,对自己的猎狗咬死了吐肯大叔的鸡,他得意的说:“哦,谁让它们跑进院里的……我的马依塔斑(猎狗名字)是能守住家门的”。这些种种表现都揭示了权力如何腐蚀了他的灵魂。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作既展示了哈萨克族人的当代生活的风情画面,又揭示了其中蕴涵的各种各样的时代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是进步的,有些则是落后的。像哈力的蜕变就是极左思潮在其身上的烙印,这也是时代潮流对哈萨克族人的影响。艾克拜尔·米吉提没有回避这些负面的影响,而是通过描写这些时代潮流对人思想品质的腐蚀,来表现哈萨克族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深入探索和反思。
他的代表作之一《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就是对美丽的哈丽黛凋谢枯槁的人生悲剧发出的深情的叹息,也是对民族文化中的陈腐观念与落后因素的反思和揭示。哈丽黛与知识青年吐尔逊江心心相印,可是哈丽黛的母亲帕夏罕大婶却一心要女儿攀高枝,为此总是在村人面前说:“我的哈丽黛呀,刚刚才满十五岁呢!”这种庸俗势利的观念,最终使哈丽黛成为“攀不上穿新靴的,看不上拖旧靴的”姑娘,一辈子没有嫁出去。往昔喷芳吐艳的红玫瑰,凋落在枝头:“她身材枯瘦,穿着一件鲜艳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黧黑的脸庞显得十分松弛,嘴角眼尾都布满了皱纹。”“在她挂满笑容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张纹路细密的蜘蛛网”。那个体态优雅、匀称,声音甜美,面貌美丽的哈丽黛已经消失了。哈丽黛的人生悲剧不是某场社会政治运动造成的,而是视女性为财物的陈腐落后观念以及家长制的淫威造成的,因而更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悲剧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哈萨克族女性命运悲剧,社会政治制度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但是人们的传统意识却无法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迅速改变。探索哈丽黛人生悲剧的根源,她母亲的阴郁、暴戾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她自身性格的软弱无力也是原因之一。新疆和平解放后,各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她们从家庭中走出来,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职业和地位。但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要求和约束还是沉重的,小说中,哈丽黛是个很能干的姑娘,“去年她在鸡鸭场搞人工孵卵,一次就孵出三百多只小鸡来。”但是在家庭中,母亲的悍厉和管束深深压制着她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性格的软弱并没有让我们歧视她而是引起怜悯,她在她的境遇中所保持的对命运的唯一的抗争就是默默地一直爱着吐尔逊江,这在她和吐尔逊江多年以后的见面中充分表现出来:“‘哦……,我衷心祝愿您永远幸福……’哈丽黛用充满痛苦的眼神看了看我,便埋下头去。须臾,她忽然抬起头来,嘴唇嗫嚅翕动着,也许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双眼已噙满晶莹的泪花。她轻轻咬住下唇,急忙扭身匆匆离去了。还没走出几步远,她的双肩就抖动开了。随即她猛然跑了起来,还隐约传来了尖细揪人的唏嘘。”这是一个无比痴情的姑娘,可是她无法反抗母亲,只能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她和吐尔逊江的爱情悲剧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在于,从中我们体察到“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3](P147)。艾克拜尔·米吉提将这种寓意融化在看似委婉、冷静的叙述中,他没有发表看似深刻的“ 点睛之笔”的议论,也没有谴责“我”的怯懦,缺乏爱的信心和勇气,也没有指责哈丽黛的软弱,甚至对她母亲都没有冷言挖苦嘲弄,但是他对造成哈丽黛一生悲剧的陈腐的观念的批判是潜藏在叙述中的,这种含蓄和隐蔽更增加了批判的力度,引发人们的思考,耐人寻味。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以“局内人”的姿态经历和体验着哈萨克族的现实生活,却保持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在的反省和思考,凭着对本民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的热爱,他积极探索着民族文化传统在时代变迁中的变与不变。他的言说是冷静委婉的,不是匕首、投枪式的犀利和无情。《静谧的小院》写的是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从中表露出来的哈萨克族特有的伦理观念和人情世故是意味深长的。古蕾芭鹤蒂从小就受父亲宠爱,结婚后,婆家所在的生产队穷,父母担心她受苦,就坚持让她和丈夫萨里回到自己家中生活,从此她在有着“两间一套,外加一间耳房,由高高的向阳长廊连在一起的敞亮房舍,和这景色幽美别致的果园”的庭院里一住就是十年。十年里,三个孩子出生了,她的大弟弟也结婚了,住在庭院里的耳房里。她从父亲异样的眼神中,开始思索弟媳对她的不满,意识到自己这样占有着父亲的庭院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因为父母都非常疼爱她,她享受了这种疼爱而不“自知”。她醒悟后,和丈夫买了另一处庭院,搬了出去。在她新的庭院中,“她发现父亲那双眼睛依然是她所熟悉的模样——从那深嵌在泪水盈盈的眼睑后面的褐色眸子里,仍旧流露着炽热的目光,使她望而顿觉心头热乎乎的。”父女间的深情依旧,一家人其乐融融。在这篇小说中,作家用一种和缓的语调不动声色地书写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哈萨克族传统意义上微妙的伦理观念和人情世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阶级斗争式的尖锐冲突,但也不是毫不利己道德理想至上的虚饰和夸张,家人之间的深情厚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微妙的和谐和冲突,呈现出了社会生活中的恒久意味的“不变”,那就是具有稳定生命力的家庭伦理观念——女儿出嫁自立门户。他其实触及到了现代化建设中的敏感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利益与家人情感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不因为经济利益的缘故,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他是以作家的敏感,感受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的私有财产观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把握得十分到位。无论是动乱的年代,还是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艾克拜尔的小说更多地是表现人们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最终以理解、宽容的方式得到解决,表现出哈萨克族丰富宽广的胸怀。《瘸腿野马》、《遗恨》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瘸腿野马》写的是“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轶事。“瘸腿野马”即喻指作为统治集团家族内部明争暗斗的牺牲品术赤汗——成吉思汗亲生儿子的悲剧命运。术赤汗已经死去,但争斗并没有结束,“合汗说了 ——如果找不到术赤汗,要把咱们钦察草原的人斩尽杀绝;要是谁敢向他报送噩耗,他就要给谁嘴里浇进滚沸的铅水!”柯尔博嘎——钦察草原最有名的琴师以乐曲《瘸腿野马》“讲述”了术赤汗的死亡经过,他临死前的懊悔、绝望与怨愤。乐曲震撼了合汗:他“高高地坐在金宝座上,一双黄绿色眼睛满含着晶莹的泪花,不知什么时候,两行泪水竟已顺着他的双颊滚落下来”——他命令:“拿过他的冬不拉!”“把铅水给我倒进冬不拉里!”滚烫的铅水终于没有灌进乐师柯尔博嘎与老兵纳雷曼的喉咙。作为暴君出现的合汗,也没有一味地凸显他的凶残,而是以一种十分符合生活逻辑的复杂感情,有分寸地表现了他性格内涵中人的温情、没有泯灭的人性的光辉。
《遗恨》这个短篇更富有复杂的人生况味。这是一个发生在古老年代的故事,贾尔肯是焦勒克的巴特尔(英雄的意思),居玛莱是巴雅洪旄下的巴特尔。他们各为其主尽忠,居玛莱一次趁夜劫走焦勒克的马群,贾尔肯与他单打独斗将他降服,居玛莱说话算数,将盗走的马群赶了回来。主人赏识居玛莱的勇敢,将他留了下来。一山难容二虎。居玛莱想悄悄离开,但在冰大坂上中了贾尔肯的埋伏。一年后,贾尔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死前他向好友承认了自己暗中袭击了居玛莱,并表达了内心的忏悔。这个古老故事其实蕴涵了丰富的现代意识,因为它具有一种现代精神——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境况以及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贾尔肯他可以战胜森林里强悍无比的大黑熊,可是他没有战胜自己的狭隘的虚荣心。他的悲剧是源于他的“过失”,他无法战胜自己性格中的弱点,结果造成了自己的悲剧命运。小说开头贾尔肯用短剑与黑熊搏斗的场面描写是在讲人与自然的斗争,在这里贾尔肯获得了胜利,可是在与居玛莱的争斗中他失去了作为巴特尔的优秀品质——光明磊落、一诺千金。作家怀着一种俯视的怜悯之情,探索由于人无法战胜人性自身的一些弱点而造成的命运悲剧。小说在这里要揭示的是某种人生哲理,有劝诫意味,也有警世的意思。
他将小说的主旨隐蔽得很深,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之根本所在。他的另一个短篇《迁墓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飞速发展,城市迅速膨胀,于是古老的墓地上要盖起一座宏伟的现代化体育馆。在这个背景下,一老一少负责迁墓。少年有力气负责刨坑起封,老人则负责进穴收骨。这两个人物是有象征意味的,而在对待墓中亡灵留下的金牙的不同态度,也蕴涵着两人不同的生活态度。老人的在意与少年人的不在意,昔日的豪商巨贾的满口金牙成为今人的一个发财梦,昨日荒凉的墓地变成今日热闹气派的体育馆……这些似乎都在给我们一些启发和警示意味。可是作者又没有将某种意旨凸现,而是留下多种空白,让读者在自己阅读的再创作中将其明确。这里,可以感受到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作其实已经超越了某种民族文化精神的限制,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于人、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天鹅》这个短篇就表达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通过一个哈萨克族小姑娘对天鹅的追寻中表现出来。孩子纯真无邪的心灵,她对天鹅的向往和追寻,还有她天真浪漫的想象,在美丽的雪山环绕的蔚蓝的赛里木湖映衬下,都构成了对美好理想、诗意人生的颂扬。
艾克拜尔·米吉提以充满现代意识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哈萨克族人的现实生活,积极探寻时代潮流中变化发展的民族精神,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个性,蕴涵着浓厚的时代气息,我们从中可以把握到哈萨克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复杂、微妙的心理发展轨迹,感受到时代潮流对哈萨克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表现作者对本民族深厚的热爱和眷恋之情。这种深沉的感情不仅表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进步因素的颂扬,而且表现在他对其中潜藏的陈腐的文化观念委婉而深刻地揭示之中。
参考文献:
[1]王蒙.序[A].艾克拜尔·米吉提.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艾克拜尔·米吉提.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A].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陈静系暨南大学博士后,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