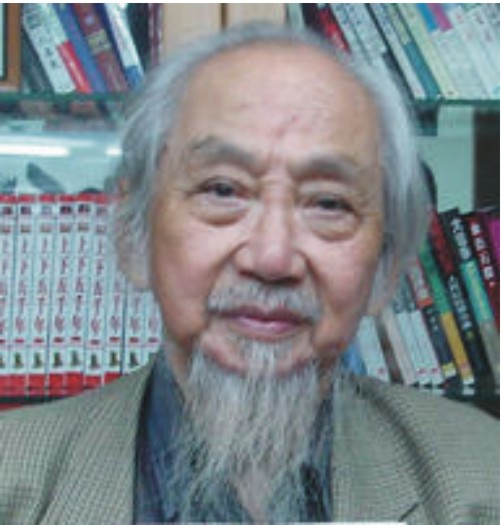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邵燕祥:我心目中的林斤澜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9-5-25 点击次数:
人们都记得林斤澜的笑脸,还有那笑声:“哈哈哈哈”,一经汪曾祺写出,大家印象相同。据说他临去时表情安详,也是含笑而逝。一直到老,双眼皮大眼睛,圆的脸,笑模样千古长存,这成为他的典型形象。
然而,斤澜像任何人一样,不能成天满脸堆笑,他不是随时都酒逢知己,酒酣耳热,或议论风生,心旷神怡,笑逐颜开,“哈哈哈哈”。
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是微皱着。
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没有当过权,没有整过人。整人往往与当权有关。人当了权,就容易膨胀,因膨胀而整人,整不听话的人,整自己认为“异己”的人。当了权的人,“官身不自由”,有时不想整人也得整人,即所谓执行上级指示,不过执行指示而整人的,也因人性不同而各有不同表现。当然,整人的也难免挨整,那是另一个问题。
老林之不整人,我以为不是因为没有当权的关系。我甚至相信,他纵令当了权也不会整人,更不会往死里整人。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的。同时,经验也告诉我,正是因此,他就注定不会当权,而注定他会是挨整的,注定他会同情无端挨整的人,以及一罪二罚、小罪重罚的人。
我知斤澜之名,是从1957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写的《台湾姑娘》始。以后每有新作,一定要浏览的,只是他惜墨如金。不过偶有一两篇发表,每每令人难忘。我现在忘记了那个短篇的题目,但一开篇,就写山村中响起了钉棺木的丁丁声,我仿佛身临其境,不但听到了一声声斧斤沉重,而且闻到了山中林木的潮气和锯末苦涩的香味。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就是说,1949年后,十年间内地的文学作品中,我敢肯定没有人写过这样的细节。
当时听说斤澜是中共党员,却不知道,这个抗战初期入党的少年,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去台湾,但从台湾归来后,却一直未能接上党的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斤澜并无党籍。过来人都知道,在那极端的年代,一个“脱党分子”,其政治地位远远低于从未入党的普通群众,实际上等于“审查对象”,说白了,就是“怀疑对象”,在“革命警惕性”的名义下大胆怀疑,可以怀疑你是叛徒,也可以怀疑你是特务。
我当时不在北京市文联,不知斤澜的具体处境。但我知道,他曾经到云南边境傣族地区去,那时叫体验生活,总之也观察,也采访,比一般的旅游要深入些。回来以后,想不到他却落下个要偷越国境叛逃的嫌疑。原来是他在当地月夜,走下竹楼散步,被同行的人告发了。由于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加上“革命警惕性”深入人心,再加上划一的思维方式,告发者的有罪推定——认为他所谓散步,正是为偷越国境“踩点”——似乎也合乎逻辑,尽管今天回头看像是一则笑话。
当时北京市文联的领导,在处理这样的告发时,没有把这可怕的笑话闹大,看来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的。若是搁在1958年以前,就很难预料。因为那时主持文联事务的田家(这里不得不点出他的名字,不然别的负责人都要吃他的“瓜落”)整人不遗余力,且采取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后来他回到陕南某地,“文革”中却被整死了,愿他安息)。也许市文联继任的干部们以他为鉴,做事得以稳当些。
我和斤澜什么时候结识,已经记不清楚。但记得“文革”以后的头一面,似乎是在一对作家朋友结合的家宴上。当在1978年夏秋,正是窒息了十年二十年的朋友们重又缓过气来的年月。我跟斤澜从那前后有了些过从。我曾到他幸福大街的家中去过,那时我辈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预约,不止一次撞过锁。但斤澜在他家门口挂着纸笔,请来访者留言,这是替别人想得周到的。
也许因为我和他走得不是特别密切,他并没向我倾诉过“文革”以至“文革”以前的个人遭遇。我向来以文会友,更从来没有对朋友进行“政审”的习惯,也就从来没问过。比如有的朋友沦为右派,二十年后重逢,我从不打听你是什么“罪名”,不愿触动陈年的伤疤,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罪名还不一样!?
斤澜对世事看得很透,所以他没有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峻急。这可不是说他没有是非。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登峰造极的极“左”暴政恶政,他在《十年十癔》一类作品当中立场鲜明,那就是判明善恶,悲天悯人。
斤澜在所谓文坛上处于边缘,人与文俱如此。“文革”以前,他不赶浪头,如果说不仅是因为对艺术的持守,也还因为身份的缘故,不免谨言慎行(但像在小说开头大写钉棺材,则在当时政治文化气氛下,又确是大胆之举)。那么到“文革”之后,大家高呼解放之际,也该放开了吧?他仍然不赶“浪头”。那时候人们都说,一个汪曾祺,一个林斤澜,他们的小说不管写得多好,也是冷盘小菜,即成不了“主菜”,在刊物版面上,“上不了头二条”。汪也好,林也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却也甘之如饴。他们的艺术自觉和相应的自信,比大伙儿前行了一大步。
有一次,在涿县桃园宾馆开一个文艺方面的会(不是九十年代初那有名的“涿州会议”),主要让搞评论和编辑的来,就文艺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也有少数作家列席,其中就有林斤澜。轮到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现在一谈文学,老是谈文学的外部关系,是不是也应该多谈一点文学的内部关系?……一言出口,大出主持会议的官员意外,有些惯于听套话的人,也满脸吃惊,这个问题提得好不陌生。会议休息时还有人交头接耳,好像林斤澜是个外行人闯进来说了些外行话:文学还有什么“内部关系”?
那次会,斤澜是由北京市文联(作协)提名参加的,做了这样不合时宜的发言以后,这类会就不怎么找他了。
我曾说斤澜终其一生是寂寞的,不是指他少在官方的会议上抛头露面,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在文体实验上和寡,那才是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才行,所谓寂寞自不待言。
他默默地写他的短篇小说,再加上晚年写些散文随笔,煮他的字,炼他的意,每个字每个意思都不是轻易下笔的。长篇大论发表自己的艺术主张,不是他的性格;偶有流露,多是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但他不是不想理论问题,有时大概想得很苦。他听到所谓“零度写作”的论调,跟他的文学观念相悖,你可以看到他紧皱眉头,质疑写作怎么可能在个人感情处于“零度”,无动于衷时实现,他的表情告诉你什么叫“百思不得其解”。我对这类问题不较真,不钻研,也不拿来“自苦”,因此我也难以助斤澜一“思”之力。斤澜有些年轻的朋友,或许能破他独自苦思的寂寞吧。
最大的寂寞,是不被理解。斤澜也是常人,自也有“被人懂(理解)”的需要。但人所共知,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任何正常和正当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斤澜晚年对《矮凳桥风情》比较满意。然而这一点不为人们留意。于是,人们好意地提到他的“代表作”,总还是说《台湾姑娘》怎样怎样。就是对《矮凳桥风情》没有异议如汪曾祺这样的老友,堪称知己了吧,他对作品本身是完全肯定的,偏偏对这组小说的题目中的“风情”二字有意见,但没把意见说透,斤澜一直耿耿于怀。我自以为旁观者清,汪老想必是联想到了“王婆贪贿说风情”,甚至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而斤澜想的却是“乡风民情”,两下里思路满“拧”了。
其实,这点没沟通还是小事,不至于太寂寞。而一切的探索都属于“征人早发”,不可能肩摩踵接,难免会踽踽独行。没有人叫好助兴还在其次,难免还会受到菲薄和冷落。有些曾经是先锋的作者,我说的是真曾作为先锋存在的,不是“假先锋”,却也耐不住寂寞,“还俗”了。斤澜从不以先锋自居,他只是默默地走自己认定的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走对”了(这个“走对”的思路犹如追求“政治正确”),而是忠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艺术理想,抵抗各样的来自权力的、世俗的压力和诱惑,从而义无反顾地,“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斤澜没能走完的这条路,是没有终点的路。
然而,斤澜像任何人一样,不能成天满脸堆笑,他不是随时都酒逢知己,酒酣耳热,或议论风生,心旷神怡,笑逐颜开,“哈哈哈哈”。
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是微皱着。
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没有当过权,没有整过人。整人往往与当权有关。人当了权,就容易膨胀,因膨胀而整人,整不听话的人,整自己认为“异己”的人。当了权的人,“官身不自由”,有时不想整人也得整人,即所谓执行上级指示,不过执行指示而整人的,也因人性不同而各有不同表现。当然,整人的也难免挨整,那是另一个问题。
老林之不整人,我以为不是因为没有当权的关系。我甚至相信,他纵令当了权也不会整人,更不会往死里整人。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的。同时,经验也告诉我,正是因此,他就注定不会当权,而注定他会是挨整的,注定他会同情无端挨整的人,以及一罪二罚、小罪重罚的人。
我知斤澜之名,是从1957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写的《台湾姑娘》始。以后每有新作,一定要浏览的,只是他惜墨如金。不过偶有一两篇发表,每每令人难忘。我现在忘记了那个短篇的题目,但一开篇,就写山村中响起了钉棺木的丁丁声,我仿佛身临其境,不但听到了一声声斧斤沉重,而且闻到了山中林木的潮气和锯末苦涩的香味。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就是说,1949年后,十年间内地的文学作品中,我敢肯定没有人写过这样的细节。
当时听说斤澜是中共党员,却不知道,这个抗战初期入党的少年,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去台湾,但从台湾归来后,却一直未能接上党的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斤澜并无党籍。过来人都知道,在那极端的年代,一个“脱党分子”,其政治地位远远低于从未入党的普通群众,实际上等于“审查对象”,说白了,就是“怀疑对象”,在“革命警惕性”的名义下大胆怀疑,可以怀疑你是叛徒,也可以怀疑你是特务。
我当时不在北京市文联,不知斤澜的具体处境。但我知道,他曾经到云南边境傣族地区去,那时叫体验生活,总之也观察,也采访,比一般的旅游要深入些。回来以后,想不到他却落下个要偷越国境叛逃的嫌疑。原来是他在当地月夜,走下竹楼散步,被同行的人告发了。由于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加上“革命警惕性”深入人心,再加上划一的思维方式,告发者的有罪推定——认为他所谓散步,正是为偷越国境“踩点”——似乎也合乎逻辑,尽管今天回头看像是一则笑话。
当时北京市文联的领导,在处理这样的告发时,没有把这可怕的笑话闹大,看来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的。若是搁在1958年以前,就很难预料。因为那时主持文联事务的田家(这里不得不点出他的名字,不然别的负责人都要吃他的“瓜落”)整人不遗余力,且采取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后来他回到陕南某地,“文革”中却被整死了,愿他安息)。也许市文联继任的干部们以他为鉴,做事得以稳当些。
我和斤澜什么时候结识,已经记不清楚。但记得“文革”以后的头一面,似乎是在一对作家朋友结合的家宴上。当在1978年夏秋,正是窒息了十年二十年的朋友们重又缓过气来的年月。我跟斤澜从那前后有了些过从。我曾到他幸福大街的家中去过,那时我辈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预约,不止一次撞过锁。但斤澜在他家门口挂着纸笔,请来访者留言,这是替别人想得周到的。
也许因为我和他走得不是特别密切,他并没向我倾诉过“文革”以至“文革”以前的个人遭遇。我向来以文会友,更从来没有对朋友进行“政审”的习惯,也就从来没问过。比如有的朋友沦为右派,二十年后重逢,我从不打听你是什么“罪名”,不愿触动陈年的伤疤,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罪名还不一样!?
斤澜对世事看得很透,所以他没有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峻急。这可不是说他没有是非。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登峰造极的极“左”暴政恶政,他在《十年十癔》一类作品当中立场鲜明,那就是判明善恶,悲天悯人。
斤澜在所谓文坛上处于边缘,人与文俱如此。“文革”以前,他不赶浪头,如果说不仅是因为对艺术的持守,也还因为身份的缘故,不免谨言慎行(但像在小说开头大写钉棺材,则在当时政治文化气氛下,又确是大胆之举)。那么到“文革”之后,大家高呼解放之际,也该放开了吧?他仍然不赶“浪头”。那时候人们都说,一个汪曾祺,一个林斤澜,他们的小说不管写得多好,也是冷盘小菜,即成不了“主菜”,在刊物版面上,“上不了头二条”。汪也好,林也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却也甘之如饴。他们的艺术自觉和相应的自信,比大伙儿前行了一大步。
有一次,在涿县桃园宾馆开一个文艺方面的会(不是九十年代初那有名的“涿州会议”),主要让搞评论和编辑的来,就文艺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也有少数作家列席,其中就有林斤澜。轮到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现在一谈文学,老是谈文学的外部关系,是不是也应该多谈一点文学的内部关系?……一言出口,大出主持会议的官员意外,有些惯于听套话的人,也满脸吃惊,这个问题提得好不陌生。会议休息时还有人交头接耳,好像林斤澜是个外行人闯进来说了些外行话:文学还有什么“内部关系”?
那次会,斤澜是由北京市文联(作协)提名参加的,做了这样不合时宜的发言以后,这类会就不怎么找他了。
我曾说斤澜终其一生是寂寞的,不是指他少在官方的会议上抛头露面,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在文体实验上和寡,那才是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才行,所谓寂寞自不待言。
他默默地写他的短篇小说,再加上晚年写些散文随笔,煮他的字,炼他的意,每个字每个意思都不是轻易下笔的。长篇大论发表自己的艺术主张,不是他的性格;偶有流露,多是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但他不是不想理论问题,有时大概想得很苦。他听到所谓“零度写作”的论调,跟他的文学观念相悖,你可以看到他紧皱眉头,质疑写作怎么可能在个人感情处于“零度”,无动于衷时实现,他的表情告诉你什么叫“百思不得其解”。我对这类问题不较真,不钻研,也不拿来“自苦”,因此我也难以助斤澜一“思”之力。斤澜有些年轻的朋友,或许能破他独自苦思的寂寞吧。
最大的寂寞,是不被理解。斤澜也是常人,自也有“被人懂(理解)”的需要。但人所共知,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任何正常和正当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斤澜晚年对《矮凳桥风情》比较满意。然而这一点不为人们留意。于是,人们好意地提到他的“代表作”,总还是说《台湾姑娘》怎样怎样。就是对《矮凳桥风情》没有异议如汪曾祺这样的老友,堪称知己了吧,他对作品本身是完全肯定的,偏偏对这组小说的题目中的“风情”二字有意见,但没把意见说透,斤澜一直耿耿于怀。我自以为旁观者清,汪老想必是联想到了“王婆贪贿说风情”,甚至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而斤澜想的却是“乡风民情”,两下里思路满“拧”了。
其实,这点没沟通还是小事,不至于太寂寞。而一切的探索都属于“征人早发”,不可能肩摩踵接,难免会踽踽独行。没有人叫好助兴还在其次,难免还会受到菲薄和冷落。有些曾经是先锋的作者,我说的是真曾作为先锋存在的,不是“假先锋”,却也耐不住寂寞,“还俗”了。斤澜从不以先锋自居,他只是默默地走自己认定的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走对”了(这个“走对”的思路犹如追求“政治正确”),而是忠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艺术理想,抵抗各样的来自权力的、世俗的压力和诱惑,从而义无反顾地,“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斤澜没能走完的这条路,是没有终点的路。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