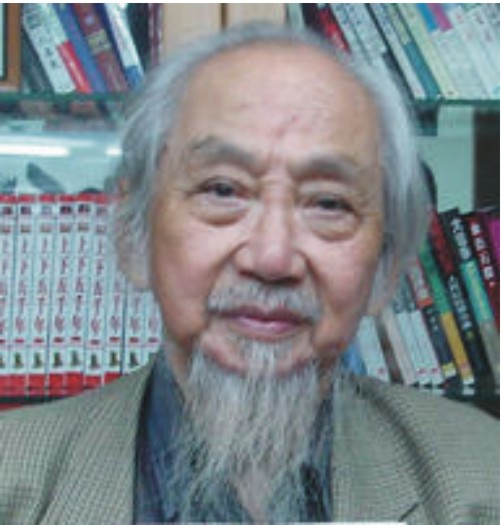文学
《场客》一部杂糅的狂欢化寓言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9-5-27 点击次数:
《场客》(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山东作家周其森最近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一个“杂糅式”的狂欢化寓言,通过韦公元这个企业家的成功与衰败之路,再现了中国从20世纪新时期直至21世纪,在面对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内在精神危机和困境。
这种“杂糅式”的狂欢,首先体现在小说的主要人物韦公元身上。企业家韦公元,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复杂体。他的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并沉积下了丰厚的商业智慧。他豪爽热情、幽默滑稽,又装疯卖傻、机敏练达。他既有纵横商场与政界的灵活手腕,权谋算计,又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有着传统儒商的仁义底线。他设计降服放高利贷的潘彩云,在市长和市委书记之间游刃有余。他精明能干,将一个村办企业,一步步发展为产值上亿元的知名企业,却在战山水等政界大腕的压榨与北京奸商田本的侵蚀下,众叛亲离,最终轰然倒下。他笃信风水,在算命先生罗洗河身上,撒下大量金钱,却又时时处于焦虑之中,充满了宿命的悲剧与生命的悲凉感。可以说,韦公元这个人物形象,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独特典型。他象征着中国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与狂欢之中,种种荒诞的人生世像,以及自身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作为一个“中国式的资本英雄”,他有着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恢弘的资本气魄;作为一个“传统之子”,他又亲善仁义,重视家族利益与亲情伦理,对自然和非理性的力量,充满了敬畏之心。然而,韦公元这个复杂立体、充满雄性魅力的“中间物”,在面对田本、都是福等猥琐的资本新贵的时候,却束手束脚,屡屡被动挨打,最终成为新世纪最后一曲凄凉的“雄鹰绝唱”。在韦公元这个失败的英雄身上,作家寄托了自己深刻的忧思和理性寓言。
其次,就小说内涵而言,该小说在嬉笑怒骂之间,却透露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文化转型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对中国独有的官场文化与商场文化的思考。小说的传统意味非常重,不但故事结构方式有着章回体的影子,而且小说中大量出现风水占卜、阴阳八卦、儒家文化等传统记忆,而“鹰兔搏斗”、“笨松”、“风水穴”等意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象征意味。作家试图通过对传统的某种回归,来解决人心道德沦丧的问题。大招子的悲惨结局,也暗示着传统道德的难以为继。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意象“广场”。“广场”在巴赫金的理论范畴中,属于狂欢诗学的空间阐释。在广场中,人们以想像的无差别狂欢,实现了酒神精神的自由意志。在近年来的很多作品中,广场,常常被作为“五四”以来激进启蒙的一个象征,被作家进行反思,例如刘庆的《长势喜人》。然而,在《场客》中,“广场”却成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尴尬文化处境的代名词。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空间,“广场”本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神话的聚集地,然而,在《场客》的“广场”,却成为流言蜚语的集中地,成为现代性匮乏的标志。小说中,不但主要故事线索之一潘彩云和韩美珠的矛盾,由广场而引发,主人公韦公元的命运与广场息息相关,而且“广场”也具有了某种预示吉凶的传统意味,成为具象的传统符号,这无疑是引人深思的。
再次,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独特的。周其森的经历非常丰富,商业、政界、学界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农村和城市生活,他也都非常熟悉。于是,小说便展现出了一些奇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他的小说语言,如同该小说的思想内涵一样,充满了杂糅化的狂欢色彩:既有山东土语与普通话的结合,也有口语与书面语的杂糅,而古音古字、乡村俚语与现代都市语言的整合,都让整部小说的信息量非常大,并带有“泥沙俱下”的话语狂欢色彩。然而,这种杂糅式的狂欢,又不同于经典意义的“小说狂欢”的定义。在巴赫金的论述中,作为一种“脱冕”仪式,狂欢化消解一切虚假的权威,将小说回归到一种自由而古老的酒神生命意志之中。而在周其森的这部小说,整体构架却是非常传统的,大多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各种语言的杂糅狂欢,一方面表现为各种能指之间的借代与错位,产生幽默的陌生间离效果(例如对狐狸、大象、老虎等代号的描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密度的故事信息含量,通过快速的故事流动,来带动语言的狂欢,而不是一种对语言本身的滞留性描述。这种叙述效果,究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发展有何启示?还有待于中国作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尝试。
这种“杂糅式”的狂欢,首先体现在小说的主要人物韦公元身上。企业家韦公元,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复杂体。他的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并沉积下了丰厚的商业智慧。他豪爽热情、幽默滑稽,又装疯卖傻、机敏练达。他既有纵横商场与政界的灵活手腕,权谋算计,又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有着传统儒商的仁义底线。他设计降服放高利贷的潘彩云,在市长和市委书记之间游刃有余。他精明能干,将一个村办企业,一步步发展为产值上亿元的知名企业,却在战山水等政界大腕的压榨与北京奸商田本的侵蚀下,众叛亲离,最终轰然倒下。他笃信风水,在算命先生罗洗河身上,撒下大量金钱,却又时时处于焦虑之中,充满了宿命的悲剧与生命的悲凉感。可以说,韦公元这个人物形象,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独特典型。他象征着中国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与狂欢之中,种种荒诞的人生世像,以及自身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作为一个“中国式的资本英雄”,他有着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恢弘的资本气魄;作为一个“传统之子”,他又亲善仁义,重视家族利益与亲情伦理,对自然和非理性的力量,充满了敬畏之心。然而,韦公元这个复杂立体、充满雄性魅力的“中间物”,在面对田本、都是福等猥琐的资本新贵的时候,却束手束脚,屡屡被动挨打,最终成为新世纪最后一曲凄凉的“雄鹰绝唱”。在韦公元这个失败的英雄身上,作家寄托了自己深刻的忧思和理性寓言。
其次,就小说内涵而言,该小说在嬉笑怒骂之间,却透露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文化转型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对中国独有的官场文化与商场文化的思考。小说的传统意味非常重,不但故事结构方式有着章回体的影子,而且小说中大量出现风水占卜、阴阳八卦、儒家文化等传统记忆,而“鹰兔搏斗”、“笨松”、“风水穴”等意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象征意味。作家试图通过对传统的某种回归,来解决人心道德沦丧的问题。大招子的悲惨结局,也暗示着传统道德的难以为继。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意象“广场”。“广场”在巴赫金的理论范畴中,属于狂欢诗学的空间阐释。在广场中,人们以想像的无差别狂欢,实现了酒神精神的自由意志。在近年来的很多作品中,广场,常常被作为“五四”以来激进启蒙的一个象征,被作家进行反思,例如刘庆的《长势喜人》。然而,在《场客》中,“广场”却成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尴尬文化处境的代名词。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空间,“广场”本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神话的聚集地,然而,在《场客》的“广场”,却成为流言蜚语的集中地,成为现代性匮乏的标志。小说中,不但主要故事线索之一潘彩云和韩美珠的矛盾,由广场而引发,主人公韦公元的命运与广场息息相关,而且“广场”也具有了某种预示吉凶的传统意味,成为具象的传统符号,这无疑是引人深思的。
再次,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独特的。周其森的经历非常丰富,商业、政界、学界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农村和城市生活,他也都非常熟悉。于是,小说便展现出了一些奇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他的小说语言,如同该小说的思想内涵一样,充满了杂糅化的狂欢色彩:既有山东土语与普通话的结合,也有口语与书面语的杂糅,而古音古字、乡村俚语与现代都市语言的整合,都让整部小说的信息量非常大,并带有“泥沙俱下”的话语狂欢色彩。然而,这种杂糅式的狂欢,又不同于经典意义的“小说狂欢”的定义。在巴赫金的论述中,作为一种“脱冕”仪式,狂欢化消解一切虚假的权威,将小说回归到一种自由而古老的酒神生命意志之中。而在周其森的这部小说,整体构架却是非常传统的,大多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各种语言的杂糅狂欢,一方面表现为各种能指之间的借代与错位,产生幽默的陌生间离效果(例如对狐狸、大象、老虎等代号的描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密度的故事信息含量,通过快速的故事流动,来带动语言的狂欢,而不是一种对语言本身的滞留性描述。这种叙述效果,究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发展有何启示?还有待于中国作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尝试。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