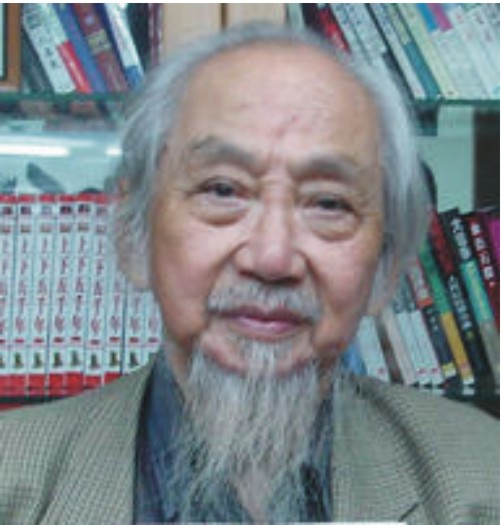古籍整理作品具有独创性,应扎紧保护篱笆
提起一个多月前的一场座谈会,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至今还气不打一处来。5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中华书局(微博)诉国学时代侵犯中华书局点校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著作权一案,邀请法律界、出版界人士座谈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保护。马建农是应邀出席的两名出版界代表之一。
“有位法学博士发言说‘古籍整理作品就不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一堆标点符号有什么可保护的?’”马建农震惊之下,立刻将《著作权法》第十二条当场念了出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马建农说:“法律有明文规定,怎么能说不受法律保护呢?”
座谈会上,不少发言者质疑古籍整理作品的独创性,进而怀疑古籍整理作品是否有著作权保护的必要。但对古籍类出版社而言,这是攸关生死的问题。如果古籍整理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出版社的相关作品将被人免费复制和使用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在网络时代,作品的复制、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和简单,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盗版行为。许多古籍整理作品未经授权便被上传到网上供人免费下载,古籍类出版社深受其害。
马建农和一些古籍专家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稿有关“文字作品”的定义里加上“古籍”,并明确“独创性”的内涵,“我们是不是需要考虑在修订的时候能够把篱笆扎紧一点?”
对此,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表示,古籍本身已经过了50年的保护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根据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等整理行为产生的作品,具有独创性,是受保护的。“实际上这个保护跟当代作品的保护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版权保护在法律上简单,在实践中复杂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古籍整理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这就需要在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确如何判定侵权。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东进就建议:“关于侵权认定,首先可以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依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果仍然没有,就依照行业惯例。这样在发生纠纷时,法官就有依据可循。”
不过,王自强认为,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保护“在法律关系上是简单的,而保护实践是复杂的”。现在的许多问题不是出在立法上,而是出在执法实践上。“人的阅历、知识不一样,对著作权的认识不一样,对作品的独创性认识不一样,就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同样的案子给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制度出了问题,而是法官在判断的时候,标准和理念有差异。”
不少专家还建议加大执法力度。因为执法力量不足,大量的侵权盗版行为难以受到惩罚,违法成本很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介绍说,香港中文大学规定,本校教授如果购买盗版图书、唱片,就会失去教职。香港中文大学还规定,图书馆的图书不允许整本付印。陈尚君说,自己搞基本文献整理,许多作品是费尽心血从众多古籍中辑佚出来的,却被人免费拿去用。“我们真应该向香港学习,提高版权保护的意识。”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说,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的问世,整理者要付出很多心血,应该得到充分尊重。我们之所以希望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能够体现出对古籍整理工作的保护,是因为古籍整理特别是原创的古籍整理工作,关乎我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关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
整理者应提高保护意识,增加学术含量
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认为,出版社和整理者也需要提高版权保护意识,想办法提高古籍整理作品的学术含量,尽可能具有独创性。他说,现在大量的古籍整理没多少学术含量,比如说断句。学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校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你千辛万苦把古人错误之处校出来了,但别人也有可能独立做出同样的校勘,你怎么去区分别人是不是参考了你的校勘呢?我们很难区分对方是做学术还是恶意盗版。到法庭上,你让法官怎么来判断呢?”金良年说。
正是由于古籍整理作品的这些特点,所以明知被盗版,权利人也很难去告盗版者。金良年介绍说,甚至有古籍整理者为了防范盗版,故意留下若干处错误,如果盗版者连错误处也照抄不误,那就成为侵权的证据了。但这种做法明显对读者不公,因此不值得提倡。
金良年建议,出版者和整理者还是要多想些办法防止盗版,就拿影印古籍来说,不能单纯拿来就影印,可以在上面加水印,对图片做修描。除了法律途径之外,金良年还建议能否通过加强行政管理的手段把质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和盗版挡在门外。他说,“国家现在规定没有资质不能做辞书等工具书,搞古籍整理难道就不需要资质了吗?我们能不能也搞一个资质认定,不达标的出版社不能做古籍整理。”